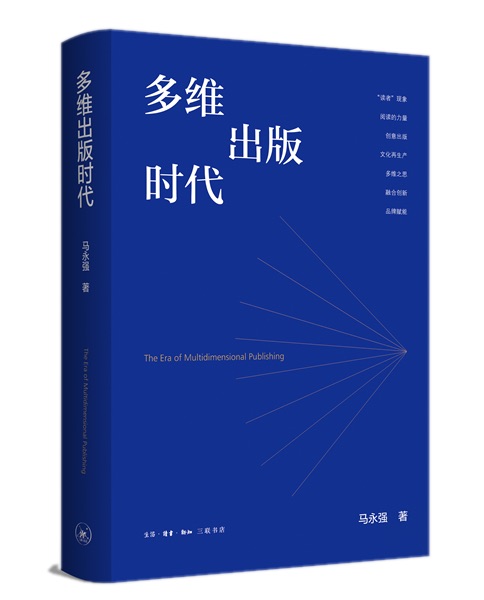语言的狂欢——《野马,尘埃》的书写与反讽
毛欣然
《野马,尘埃》是冯玉雷先生2020年出版的敦煌题材小说。小说围绕着安史之乱前后唐朝、吐蕃和周边众多民族家国的互动展开描写,鸿篇巨制,体大而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文学方面的实践。

“语言学转向”是20世纪哲学的巨大变化,对紧随哲学的其他社会学科如文学艺术产生巨大影响。文艺批评也随之转向语言学批评,语言学转向是当代众多文学艺术流派的滥觞。语言学成了哲学、思想和文学艺术的根本问题。冯玉雷以小说创作的形式回应这一趋势。在《野马,尘埃》中,语言是关键、根本、本位性要素,是故事情节展开的形式,是人物的生存方式和存在价值,是民族交往、文化交流的呈现形式。语言是想驰骋飞扬的载体,是主人公对抗艰难的生活处境,追寻心灵慰藉和解脱的方式。怀特海在《思维的模式》中论述作为思维表达方式的语言:
在所有表达思维的方式中,语言无疑是最重要的。人们甚至会认为,语言即思维,思维即语言。因此,一个句子就是一种思维。1
语言是最重要的表达方式,语言表达了思维,甚至被认为是“思维”本身。当代西方文论中一个重要话题就是“语言学转向”,哲学、美学、文学、人类学等众多人文学科都转向语言学问题。该转向从索绪尔开始,索绪尔说“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言语活动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重要。” 2 索绪尔指出语言符号是任意的,符号具有不变性和可变性的特征。构成任何语言都必须有大量的符号。所指和能指关系可以转移。《野马,尘埃》 3 中充满了语言符号,重要符号的所指具有多义性,如“野马”“尘埃”“大痣”“尚修罗”等,这些符号的意义纷繁复杂。
语言可能招来祸患,荀子说:“言有召祸也,行有招辱也。”(《劝学》)司马迁说:“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报任少卿书》)尚修罗的语言超能力带来的是长达十二年的囚禁,造成了大青牛狂奔事件。《野马,尘埃》全书以尚赞摩给赤松德赞的一封请罪信开始叙述。尚赞摩向赞普建议在占领地实施统一语言的政策,将唐语及南诏、突厥、白兰、苏毗、多弥、党项、羊同等众多语言统一为吐蕃语。语言统一才方便文化交流,在多民族交汇之地中国西部,多文化碰撞,语言交汇,在民族交流融汇的大背景下,语言承担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文书以多种语言记录,负责翻译的牙郎也是受欢迎的职业。尚修罗攻下敦煌后,继续推行其父“讲蕃语”的语言政策。大将军尚修罗每次演讲,都围绕推广语言话题展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铸牢首先体现在语言的交融上,小说描写的语言统一政策的效果可以在后代历史中得到印证,晚清刘赞廷 4 的康藏方志中记录了藏汉“混合语言”,即说话时将藏、汉词汇混合使用。
本文围绕着《野马,尘埃》的复杂语言学问题展开探索,此处“语言学”并非狭义概念,而是包括叙述、书写、笔法、仿效等众多内涵的“广义语言学”。
一、传统笔法书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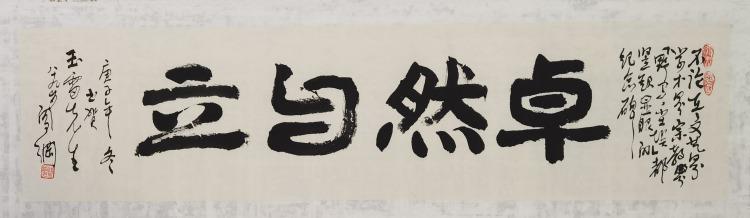
《野马,尘埃》的语言广泛吸收了《庄子》、史书、佛经、多民族、古今方言、契约文书等众多书写形式与内容,呈现了语言狂欢、众声喧哗的特点。作者故意设置语言障碍,增加阅读的距离感与难度,只有敲破艰涩的语言外壳,才能探知小说的精髓。
冯玉雷效法史书(如编年体或纪传体)的书写方法。尚赞摩书信中使用大量冗长的修辞,如排比。语言力求繁复,避免简洁。有汉大赋的铺排,辞藻华丽夸张的语言特色。《宁布桑瓦》篇叙述手法类似编年体史书,按照皇帝年号、年、月逐条记录大事件。叙述者“秉笔直书”不带个人感情色彩。史书书写还体现在结构上。在主要故事情节结束后,作者设置《捉笔舍人列传》并以某某舍人叙录为小标题。早期“叙录”是在书后的,如《庄子》最后一篇《天下篇》具有叙录色彩,《史记》《汉书》的叙录都在书末。《野马,尘埃》舍人叙录位置靠后,是对传统史书笔法的继承。互文是纪传体史书的常用笔法,也是《野马,尘埃》的重要书信手段。故事开场尚修罗年纪12岁,十二在中国文化中也是一个具有文化内涵的数字。于古文中可以是虚数代表多,还可以是12地支,12月,12生肖等。
主角尚修罗姓“尚”,尚古与“上”通用,古代可以把皇上简称“上”;尚还有尊崇、古老、久远的意思。姓氏来源于姜太公,或说出自姒姓,夏部落尚黑,故后世以“尚”为姓。同时“尚”是唐时吐蕃的姓氏,这符合主角的身份。总而言之,尚修罗这个名字充满象喻。
《野马,尘埃》从中国传统笔法中广泛吸取营养,对于传统故事、典故、经典等的使用达到了化境的程度。如夫蒙灵察遭遇“鬼魂兵团”时间化用李华《吊古战场文》“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下面笔者从《庄子》、佛经、身体、民族书写四个方面简要分析:
(一)《庄子》书写
《野马,尘埃》不但大量使用的《庄子》中寓言意象,还使用了大量《庄子》笔法 5。《庄子·逍遥游》一句“野马也,尘埃也”历来注释家有不同见解。晋·郭象注“野马者,游气也。”晋·司马彪注“野马,天地间气。如野马之驰。”唐·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三“野马”孙星衍校正:“或问:‘游气何以谓野马?’答云:‘马,特塺字假音耳。野塺,言野尘也。’”《说文·土部》:塺,尘也,从土麻声。和“马”上古音接近,可以通用。此外,闻一多猜想:野马是野外之尘。尘埃,是室内之尘。故“两称而不嫌”。还有学者认为“尘埃也”乃注释误入正文。《庄子》的“野马、尘埃”,即佛典所谓“炎气”又叫“阳焰”。“野马”还可以造成海市蜃楼。6 冯玉雷抓住“野马”“尘埃”解释的不确定性加以发挥,以上诸多义项和意象都为作者采纳,使其成为贯穿全书的多义性符号象征,并赋予其繁多而复杂的涵义。
《野马,尘埃》以《庄子》中的寓言意象构建自己的神话体系。不但使用了“野马”“尘埃”,还以庄子神话中的“倏”“忽”“混沌”对应小说人物,更使用了《庄子》哲学思想的深意和重要注本的解释。《庄子·天下》曰:“历物之意,曰:‘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成玄英疏“心游万物,历览辩之。”“囊括无外,谓之大也;入于无间,谓之小也;虽复大小异名,理归无二,故曰一也。”陆德明《经典释文》解释为:“形之外为无,无形与有,相为表里。”7 《青木部》尚修罗的叙述就体现了这种思想。尚修罗被囚禁在驼骄中,空间很小,身体不自由,但却可以“心游万物”;或者说正因为身体被束缚,才促成尚修罗努力开发意识的力量。尚修罗可以身体坐在驼骄内,而心灵意识飞驰到千万里之外看到彼处所发生的事情。尚修罗可以听到各种言说声音,即使觉得吵闹时也无法屏蔽。他的意识甚至可以使外界发生混乱。后来尚修罗的精神分裂成无数个——野马朕、尘埃朕、白色朕、黑色朕(朕是尚修罗的自称)……真实身体始终没有离开驼骄,意识中的身体却历尽艰险,走到痛苦和崩溃的边缘,尚修罗的意识再分裂,分出一个上帝视角,高高在上地看着自己身体受苦,看着倏(也是尚修罗)和忽为安禄山凿七窍。尚修罗的内外有无不但相互解释,互为表里,而且极尽“谬悠”“荒唐”之能事,把庄子寓言、重言、卮言的笔法用到极致。
“大痣”在《野马,尘埃》中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小说中很多人物身上都有大痣,它可以移动。大痣成了如“野马”“尘埃”般极具多义性的符号。《庄子·逍遥游》曰:“《齐谐》者,志怪者也。”“志”义为记载。“志”“痣”同源,都有标记的意思。古书中“志”或通“痣”。大痣作为一种标志和象征,还具有记载的含义,它在小说中被赋予极多的意义可能性,是权利、欲望和罪恶的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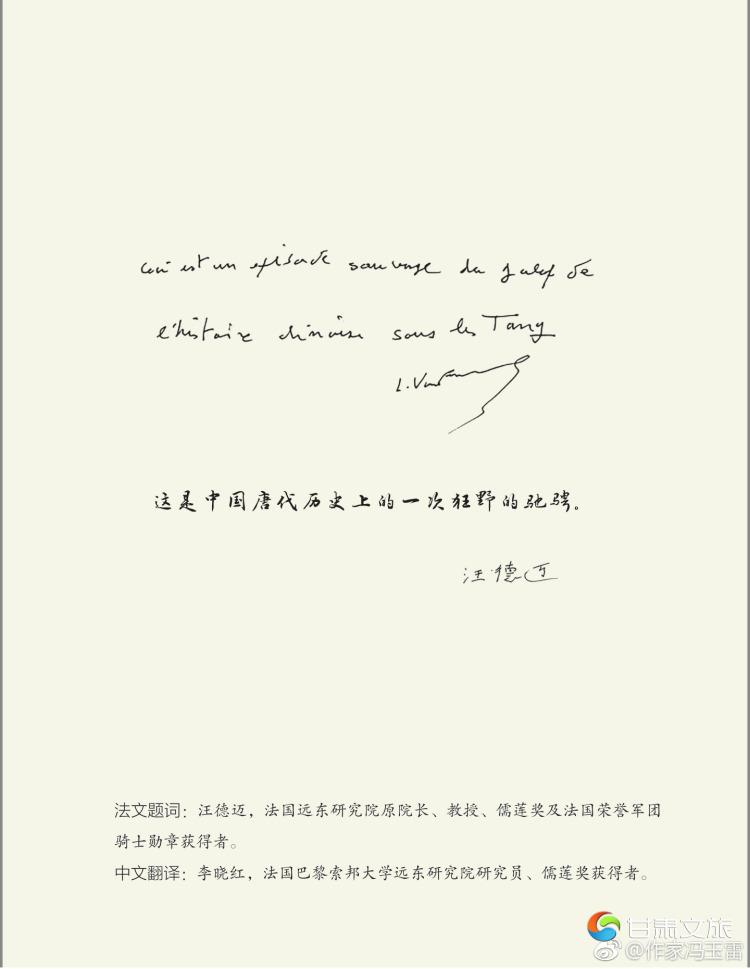
《野马,尘埃》中的第一人称是混乱的。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方言(包括古代方言)、民族语言并存,如“卬”“曹”“阿咪”等。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朕”。朕,从舟,灷声,本义是舟的裂缝;还有预兆,迹象之义。从秦始皇开始,“朕”成了皇帝的专属自称,而秦始皇之前,朕字在甲骨文、西周金文中习见。“朕”是带有楚国方言色彩的普通自称。《庄子·应帝王》写道:“鸿蒙曰:浮游不知所求,……朕又何知!”“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而游无朕”郭象注“任物,故无迹”,成玄英疏“虽遨游天下,接济苍生,而晦迹韬光,故无朕也。”8 无朕就是无我,即《逍遥游》所谓“至人无己”,庄子认为最高境界是与宇宙大化融为一体,弥合无我之分。“朕”有预兆、迹象的意思,“应帝王”的篇名、核心语言倏忽混沌都与“朕”有隐含联系。而第一个和最有代表性的“朕”的使用者就是尚修罗,他的精神遨游千里,但无论囚禁中还是释放后都被各种烦恼缠绕,没有达到“无朕”的哲学境界。“朕”这个第一人称正寓示了小说人物当时的不自由,不能逍遥游。尚修罗在被囚禁和彷徨苦闷中用“朕”自称,其他人物也往往在处境危险、精神混乱时使用“朕”。屈原的“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离骚》)也是“朕”的隐含话语,隐含作者用这个“朕”暗中提醒人物悬崖勒马,即时回头,不要走向穷途末路。先秦诸侯用“孤”“寡”“不榖”等谦称自称,秦始皇开始自称“朕”,表示自己开创了超越三皇五帝的功绩,是尊称。当今网络用语以“哥”“姐”自称,小说中的人物也往往自我尊称为“爷”“哥”“姐”“阿咪”,《野马,尘埃》第一人称的复杂既有历史渊源,又是对当今网络用语的映照。
贯穿《野马,尘埃》全篇的“倏忽”故事即出自此段之后。尚修罗被唐俘称为野马王子,虽然尚修罗为将军之子,非王子,但曾经代替悉勃野小王子在回纥为质子,出生七天后更名为“倏”。“倏”“忽”在全书中特别具有神秘色彩,其到底为何始终没有明言,和“野马”一样,具有多义性和神秘性。
(二)佛经书写

尚修罗名之“修罗”出自佛教“天龙八部”之第五部阿修罗。阿修罗是文学和影视作品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因为这个角色善恶并存,十分复杂。阿修罗是欲界天中半神半人的大力神,男阿修罗好斗易怒,经常与诸天战斗,是佛教的战神。女阿修罗貌美,迷惑众生。阿修罗虽然本性善良,但常常带有嗔恨之心。作者给主角起了这样的名字,赋予其复杂丰富难以言明的内涵。这与书的标题“野马,尘埃”是相呼应的。“永徽三年……三月,‘混沌甲号’从秘密藏匿地发出百种和谐悦耳之歌乐,弥漫雪域。苯教师及信奉者则说声音来自某个婴儿,其发出恐怖呐喊:‘我叫尚修罗!我要射杀赞普!’”9 这一段与尚赞摩请罪信所叙述的内容形成互文,“赞普”是吐蕃之王,相当于唐之皇帝,皇帝可以被称为“天”,赞普也可以相当于“天”。这个情节又暗合阿修罗挑战诸天。按照常理,婴儿不能发出“呐喊”的行为,但尚修罗从出生即开始表现出各种奇异,如口述《宁布桑瓦》。作者赋予《宁布桑瓦》预言书、神书、宗教经典的内涵,它神秘又广受追捧。它有教化唐俘,避免暴动、哗变、逃亡、抗命之类的作用,还使吐蕃军控制陇西,收获唐朝土地、人口,作用巨大。简直如宗教圣物般神奇。
《野马,尘埃》又仿佛经写法,不厌其烦地讲述,有的情节甚至会重复,但叙述角度不同。每一部的结束和下一部的开始,事件会有重复,如《白金部》结束在安禄山造反之后,是概述;《青木部》开始则详细叙述造反前太宗为安禄山开凿七窍的过程,是详述。又如描写蒹葭怀孕生产:
在尚修罗之母蒹葭受孕前、受孕、孕育乃至分娩整个过程有多少色兆、香兆、味兆、触兆……那时,兼葭大腹便便,濒临生产。密诏到达石堡城时,天空飘香,花雨缤纷。受其祥瑞感召,兼葭胎动。10
小说在佛经的影响下形成反复的笔法,借以达到特殊艺术效果,如讽刺,明清小说既有如此笔法,如《西游记》七十九回:
假僧接刀在手,解开衣服,挺起胸膛,将左手抹腹,右手持刀,唿喇的响一声,把腹皮剖开,那里头就骨都都的滚出一堆心来。唬得文官失色,武将身麻。国丈在殿上见了道:“这是个多心的和尚!”假僧将那些心,血淋淋的,一个个捡开与众观看,却都是些红心、白心、黄心、悭贪心、利名心、嫉妒心、计较心、好胜心、望高心、侮慢心、杀害心、狠毒心、恐怖心、谨慎心、邪妄心、无名隐暗之心、种种不善之心,更无一个黑心。
从佛经到传统小说再到冯玉雷的《野马,尘埃》,繁琐叙述愈演愈烈:
朕(尚修罗)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朕何时开始分裂为“黑色朕”和“白色朕”?新的分裂会不会继续?分裂何时终止?如果整体版的朕有始无终地分裂,会不会产生“唐朝朕”“吐蕃朕”“大食朕”“回纥朕”“南诏朕”“高句丽朕”“新罗朕”“玄宗朕”“赞普朕”“可汗朕”“酋长朕”“节度使朕”“火拔颉利发石阿失毕朕”“阿布思朕”“葛腊哆朕”“李失活朕”“默啜朕”“勃德支朕”“余塞匐朕”“可突干朕”“白山榦態朕”“黑水勒潮朕”“野马朕”“尘埃朕”“白金朕”“青木朕”“黑水朕”“红火朕”“黄土朕”“八卦朕”“十天干朕”“十二地支朕““十二星座朕““四微尘朕““顿悟朕““渐悟朕”“七色朕”“狗肉朕““利牙朕”“酷刑朕”“慈悲朕”“利益朕”“钩心斗角朕”“伦理混乱朕”“毒焰朕”“冰窟朕”……11
尚修罗分裂成无数个“我”,读来滑稽可笑。作者故意繁复地叙述,用以讽刺。通过比较,可以看到《野马,尘埃》对传统小说笔法的继承。
(三)身体书写

《野马,尘埃》还描写了奇特残忍的身体书写,从而体现了诗歌为信仰的传统。在《立秋卷·范舍人叙录》中,敦煌被吐蕃围困期间,人们以诗歌作为“敦煌与内地的最后联系。”12 人们狂热地喜爱、崇拜、信仰诗歌,甚至进入宗教活动般迷狂的状态。很多年轻女孩自愿献出身体,作为范舍人的书写工具,配合范舍人用各种残忍的手段,如用灯台红蜡泪烫,用牙齿咬,用指甲文,用刀刻,把诗歌书写在身体上。舞女们心甘情愿,激动得忘乎所以。对于这些诗歌文字歌儿舞女们“曾经视同生命”13
(温五娘)那时,我们很年轻,看不到未来,便狂热地追求奇特发型、奇装异服和时尚行为方式,当酒客们在明月当空的夜晚齐声朗诵你写在舞娘们前胸后背大腿小腹上的诗歌,当我们激情尖叫忘乎所以时……
(小朱龙格)那次,你没有用毛笔,也不用墨汁。你举着龙城灯台,让连续滴落的红蜡泪在卬身体上烫出《玉女泉咏》……14
这种疯狂的信仰中伤害和自残行为如同宗教仪式的迷狂。弗雷泽《金枝》中描写祭祀阿蒂斯的仪式:
祭司长把自己的手臂割出血来,作为祭品上供。奉献鲜血作祭品的还不止他一人。铙钹撞击,鼓声轰鸣,号角呜咽,笛声尖叫,下级僧人受到狂野音乐的刺激,飞旋地跳着舞,摇着头,散着发。等到欢乐进入狂热状态,感觉不出痛苦了,他们用磁瓦片或刀子将自己的身体本划破。让祭坛和圣树染满他们流下的鲜血。……就是在这个“血日”,为了同样的目的,新僧人进行自我割阉。当宗教激情鼓动起来进入高潮时,他们便动手割阉并把自身割下的东西向残忍的女神像上猛砸。
希拉波利斯每年这一盛大节日……人群从叙利亚以及叙利亚邻近地区涌来女神圣所。……祭司们自己拔出刀来进行阉割。这种宗教激情像浪潮一样在观众中扩散着,很多人忘了自己是欢度节日前来看热闹的观众,竞情不自禁地也效法起来。15
随后,弗雷泽写到“激情过去,冷静下来,对于这样无法挽回的献祭,此人将终身为之痛悔长恨。”16 在宗教迷狂下冲动的行为引来悔恨,类似的情节也出现在《野马,尘埃》中。冯玉雷不但描写了如宗教迷狂般的诗歌信仰,还解构了信仰,描绘了信仰的失落。舞女们忘我崇拜的诗人范舍人其实是个剽窃者。他的激情书写并不是即兴创作而是窃取了毛押牙、马元奇的诗歌。这些诗歌变成了舞女们无法抹去的耻辱:
大红春伤感地说:……当时,我多么崇拜你啊!毛押牙、马元奇被逮捕后,我们才发觉被你可耻地骗了!你必须赔偿我精神损失费,并将那些曾经的狂热和崇拜感全部清除!
小朱龙格哭泣说:……那种刻骨铭心的疼痛!你为什么要在蕃兵围攻敦煌时以这种方式欺骗大家?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
洛儿殷淡然说:曹认命了,这是前世造的孽。……占卜师说了,曹念诵《瑟瑟咏》十万遍,那些字迹就自动消除,不会带到来生去……唉,当初,你在刀尖上抹了啥药?文的印痕真深刻,没有一点变化的迹象……17
曾经被奉为比生命更重要的珍宝竟然是赝品,抄袭,舞女们的精神遭遇巨大打击,信仰变成了如今想尽办法无法消除的痕迹。身体上的痛苦很容易恢复,信仰的崩塌则是天崩地裂的大事情。当信仰变成笑话,人生何其残忍。这些内容呼应了标题“捉笔舍人列卷——现实是不是有些太血腥”。
把诗歌作为信仰是一种传统的诗歌观,它与现代人的诗歌观念截然不同。今天,诗歌是一种纯文学体材,能写诗或者是一种锦上添花的点缀,或者是诗人的职业、工作,诗歌可以是兴趣爱好,却没有人将其当成信仰。中国传统社会却并非如此,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诗是“言志”的,是人生理想抱负的呈现——“文以载道”,文人用诗文承载儒家道统;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具有强大社会功用。从先秦《左传》中“三不朽”的“立言”到唐代全民皆诗,诗歌是诗人生命和血肉的凝构。即使到了民国时期,在传统文人的观念中仍然如此。罗志田论述民国四川的“五老七贤”时有言:“但对其个人和数量不大的追随者而言,诗文的好坏似乎仍是他们非常重要的关怀。”18 而这些传统文化人受到新文化的冲击,不再是社会的主流,他们乡居养老,寄情于诗文。诗歌既是他们的生活交往方式也是他们生命的呈现方式。冯玉雷以小说中荒诞的情节展示了把诗歌作为信仰的传统观念。
(四)民族书写

《野马,尘埃》不但吸收《庄子》、史书、佛经等书写笔法,还融汇了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索绪尔说:
语言学和民族学的一切接触点,语言史和种族史或文化史之间可能存在的一切关系。这两种史总是混杂在一起的,彼此之间有相互关系。19
民族和语言交融甚至混杂在一起。民族的问题也是语言的问题。颉利被俘,太宗赐以田地房屋,授右卫大将军,并建议他号召部属为大唐安定团结效力。颉利声称要远离纷争。此后“颉利在受封土地种草,每天骑黑色大公羊在草地上玩耍,风雨无阻。他将多余草拔下,晒干,打捆。”20 作者使用了“一个坐在黑公羊上的人”的意象。西藏孔麻老母管辖阴间妖魔,身穿黄袍,手持金钩,坐骑公羊。“贞观八年……七月,颉利从黑色大公羊背摔下,受惊而死。唐太宗赠归义王,谥曰‘荒’,并下令用颉利积累之干草按突厥习俗在渝桥边火葬颉利。仪式中,黑色大公羊模仿狼嚎叫,力竭而死。”21 怪异的现象预示着不详。骑乘黑色公羊的人是阴间的妖魔,黑色公羊模仿突厥图腾狼叫,这些都是兵乱和唐朝衰落的预示。
尚修罗围困敦煌之际,卓夏(继承了父兄大量遗产的吐蕃女)突然声称要嫁给敦煌城主阎朝,这件事促进了吐蕃敦煌结盟(或者说敦煌投降),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围困。对于卓夏嫁给阎朝时间,吐蕃和敦煌两方面各种势力都表示不能理解,尚修罗不置可否,卓夏事件成了小说中又一符号性表达。汉族男与西藏女的联姻是一种历史共性事件,在汉族和藏族交接地域广泛地发生。如清代刘赞廷多种康藏方志即有记载。
尚修罗的形貌:头上有角、黑色或(尚赞摩言尚修罗出生时眼睛像给珍珠)者蓝眼睛(尚修罗意识混乱中自述“朕的蓝色眼珠”)、暗红色大痣(鼻梁或者尾骨上),舌头上有苏特文等多种字母,出生时脖子上就有七色吐蕃铭文项圈。该项圈与尚修罗的语言能力和意识超能力有联系。囚禁驼轿期间十数年形体如刚出生的婴儿,被解除囚禁后变成高大威猛的将军。开凿安禄山的倏是否为婴儿未知,文中没有对其正面描写,只通过分裂后尚修罗的眼睛看到倏长得和别人都一样。
尚修罗在石堡城大帅府邸出生时,最先露出半截尖角。卑职吓坏了。接着,又看见天灵盖、额头、耳朵、眉毛、眼睛——他的眼睛黑又亮,如同两粒珍珠,又像秋天的青海湖光泽闪耀。22
通过其父尚赞摩给赞普书信可知,尚修罗在出生时头顶即有角。被囚禁的尚修罗在极端想看一眼女巫阿史德的正面时,自己幻想头顶长出独角:
难道,连看一眼阿史德的愿望都不能实现吗?朕想象头顶长出昆仑山般粗壮之独角,然后,奋力向尖刀丛形成的圆环撞去。一声震天巨响,独角意外地撞击到转向中的俏丽背影上,震耳欲聋。23
索舍人索性大声爆料:“大元帅如果不打仗,头上就会生出野牛角!”……连续大喊:“尚修罗与女人同居,头上也能长出野牛角!”24
尚修罗幻想中独角的活动对现实产生了影响,全书虚化与实有难分难解。文中多次出现的“我要刺杀牛魔王”的疯狂呐喊,据说“牛魔王”就是尚修罗。25 预言中尚修罗刺杀赞普,众人想刺杀尚修罗。
牛头人身是神农,即炎帝的形象。神农氏生长于姜水,“姜”即牧羊女,与羌(牧羊人)同源,中国古代的“羌”不同于今天的“羌族”,是生活在我国西北西南广大地区的游牧民族的总称。羌对中原文化有重大影响,除炎帝外,黄帝之妻、大禹等众多先贤都和游牧民族有联系。李泽厚认为青铜器上的饕餮是牛头纹。“此牛非彼牛,而是当时巫术宗教仪典中的圣牛。解放后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表明,牛头作为巫术宗教仪典的主要标志,被高高挂在树梢,对该氏族部落具有极为重要的神圣意义和保护功能。”(《美的历程》)牛头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信仰图腾符号,尚修罗头上有角的特征述说了他的民族象征,传达的是我国西部众多民族的声音。
此外,《野马,尘埃》还把学术研究内容写入小说,在敦煌学中契约文书、写本文献受到了学界的重视,冯玉雷在《火红部·围敦煌·天版卷》中专门记录“五件契约”,分别为甜、酸、苦、辣、咸契,又附繁琐批注。把契约、公文与小说完美融合。
二、言说与反讽

《野马,尘埃》既有对传统书写笔法的继承,又有对西方小说技巧的使用。作者在“后记”中自述非常喜欢探究小说的技法,《野马,尘埃》可谓小说语言的实验室。小说的叙述语言充满了荒诞、滑稽和深刻的反讽。讽刺的对象可能是主要人物、次要人物(皇帝、高官、英雄……)也可能是当今社会的歪风邪气。
(一)戏访与反讽
戏访或称戏拟是“从文体学和风格学上看,戏仿可以简赅地界定为‘不协调的模仿’,是‘滑稽’(Bur-lesque)的一种手法或变体。其目的在于通过突出形式和风格同题材之间的悬殊或落差,造成一种滑稽可笑的效果。”26 小说家可以访传统、历史、经典,也可以访后世、当今,通过不和谐的描写达到反讽的效果。冯玉雷在文中融入网络语言,模仿当今社会跟风、戾气、哗众取宠等不良现象,再以夸张的笔法呈现出来。
如果说第一部,作者的讽刺主要集中在唐王朝,那么第二部的讽刺则几乎指向所有人物。荒诞在第一部只是调味剂,到了第二部就成了主旋律。“骆驼们相互推诿,拒绝上岗。”27 有的时候讽刺没有具体对象,而是不良社会现象。骆驼当然不会真的推诿,只有人才会如此。
拉着驼轿的骆驼累倒了,没有骆驼接替,奇异事件发生,与骆驼连接的驼轿并没有倒下而是悬浮。这一异象引起了吃瓜群众看热闹的热情,像观看荡秋千杂技一样欣赏,由此引起了被囚禁在驼轿中的尚修罗对于荡秋千表演的联想。纤细的丝绳荡起了千军万马。小说中充斥各种网络词汇“摆POSE”“哇塞”“太雷人了”……尚修罗还模仿解说词方式为荡秋千解说,有奖竞猜“大家猜猜看,谁将成为新的荡主?帝俊?羲和?不对,大家兴奋起来,狂热起来,再猜!”“观众如同表情凝滞的冷漠群雕,尖叫声却一浪高过一浪。”“观众的表情、肢体等外在语言与源自心灵的呐喊错位了。”28 这就如当今狂热而冷漠的网络一样。作者通过疯狂荒诞的描写,处处讽刺当今社会之怪现象。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描绘晚清社会黑暗的现实。《野马,尘埃》则通过虚幻的笔法影射当今社会方方面面“怪现状”。
作者对忠勇之士的态度是温和尊敬的,同时人物是圆型的。哥舒翰是著名大将军,但他早年嗜赌晚年淫乐洗澡中风。哥舒翰早年好赌,作者以一贯夸张手法描写狂赌。哥舒翰成名将后,还不时有人希望和他赌博。玄宗为安禄山开凿七窍时满朝文武都带着滑稽的混沌面具,哥舒翰不在场,因为他中风了。安禄山七窍开凿完成,哥舒翰突然惊醒,穿着睡衣疾驰到大殿大喊“反了反了”,在所有官员不敢说出真话的时候讲真话。玄宗在逃跑过程中发现哥舒翰不住在自己赐给他的大宅子里,而是住在小巷子里,可见其生活俭朴。玄宗重用哥舒翰平叛乱贼,哥舒翰很感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但是打仗过程中,明知上级要求的出潼关是错误的,有高仙芝、封常清的前车之鉴,哥舒翰不敢抗命,只能“恸哭出关”,终于失败被缚。叙述者驼轿和傀儡人阿嗜尼都对哥舒翰报以同情态度。被俘虏后因为中风,无法说话行动,安禄山命人伪造劝降书劝降哥舒翰的部下。最终哥舒翰和部下被安庆绪杀死。哥舒翰被杀前阿嗜尼企图阻止,但最终无用。驼轿和阿嗜尼都曾祈祷让哥舒翰像个英雄那样死去。驼轿和阿嗜尼一定程度体现了作者对英雄失路的遗憾。被砍头后“哥舒翰、左车等人摸索到各自的头颅,抓起抱在怀里,向东方迈出稳稳当当的步伐,高声朗诵:‘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哥舒翰等跨出七步,陆续倒下,引发地震,凝碧宫剧烈颤抖。”29 哥舒翰死后的描写再度魔幻。被砍头者抱着自己的头颅,该情节用《三王墓》中眉间尺自割头颅递给黑衣人的典故,充满了悲壮色彩。英雄倒下,天地为悲。
(二)狂欢与反讽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道:
现实社会的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30
大众文化和社会公共话语都向消费化发展,大众传媒把人们的审美趣味引导向浮浅和碎片化。冯玉雷对于当今社会过度追求娱乐的现象也有讽刺,《野马,尘埃》中大肆描写舞蹈和狂欢,皇帝、大臣和百姓都极力追求娱乐。
贞观八年……八月十五日,九成宫宾客云集,莺歌燕舞,文成公主与弘化公主顾盼自若,神采奕奕,在丝绸莲花垫所托之“混沌”上,或表演优美动人之宫廷舞,或跳欢快激烈之胡旋舞,各国嘉宾,赞不绝口。第七日,达延芒结波上前致礼时,某颗“混沌”忽然发出响亮鸣叫:“德嘉沐!”31
王充在《论衡·异虚》中说:“夫王者有过,异见于国。”32 国君耽溺于歌舞,上行下效,狂欢、跳舞、取乐……在种种乐事中,不详正在滋生。混沌鸣叫之语是吐蕃新创的语言,此处预兆唐朝衰落,吐蕃强盛。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过度追求欢乐、繁华的背后,各种黑暗和不详涌动,这就是盛唐。作者大力描写唐朝之全民狂欢和霓裳羽衣曲之的惊艳和其带来的喜好歌舞的社会风尚。后来中唐诗人白居易在《霓裳羽衣舞歌和微之》描写该舞蹈之美妙:
我昔元和侍宪皇,曾陪内宴宴昭阳。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舞时寒食春风天,玉钩栏下香案前。案前舞者颜如玉,不著人间俗衣服。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纍纍佩珊珊。娉婷似不任罗绮,顾听乐悬行复止。
磬箫筝笛递相搀,击恹弹吹声逦迤。
诗歌描写唐宪总元和年间事,白居易曾参加皇宫宴会,“千歌万舞不可数”舞蹈还搭配熏香,舞者服饰仿佛仙女。诗歌还描写了舞者华美的配饰,舞女美好娇弱,随着音乐舞步或行或止。乐器伴奏用的是磬、箫、筝、笛等配合的交响乐。从白居易此诗可知《野马,尘埃》的歌舞狂欢乃艺术之真实。
全书叙述信息密集,还呈现众声喧哗的复调特征。每个叙述者讲述的内容多有出入,全文没有任何一个客观的叙述者,如同实际生活中,每个人讲话必然从自己的角度、利益出发。尚修罗身体被囚禁在驼轿中,只好让思想驰骋。由于尚修罗的无聊和努力,出现了其思想影响现实的异事。尚修罗一直叙述到被从龙城抛到长安,亲眼目睹了安禄山开凿七窍的经过,最终安禄山造反,倏和忽被囚禁在长安。大将高仙芝和封常清因为奸臣谗言被玄宗派人杀死。叙述者尚修罗的年龄扑朔迷离,第一部故事开始时尚修罗12岁(尚赞摩给赞普的信说起出生七天后失踪12年),而第二部尚修罗自述到三岁,后年龄越来越混乱。“九年后,‘白色朕’带着夫蒙灵察,沿着原路返回凉州。一来一往,两条曲线即便是拐弯抹角最多的地方也都完全重合,令人叹为观止。‘黑色朕’对此将信将疑。”33 如果从三岁开始,“倏”跟随夫蒙灵察时隐时现,9年后到长安刚好12岁。但是文中并非只有这一种叙述。由于尚修罗的分裂,其所言带有大量虚幻色彩,很多信息自相矛盾。如“夫蒙灵察奉诏入京,历时五年才抵达长安”34 那么尚修罗在龙城驼轿中度过几年?被夫蒙灵察接管后又几年?按照其自述分裂,一个跟着夫蒙灵察迷路,一个继续在龙城街道上运动,直到某天尚修罗被欢呼的人抛上天空落下时到了长安,至此分裂的尚修罗仍然没有统一。
心理疾病中有“精神分裂”,即日常所谓“疯了”,还有“人格分裂”,一个人分裂出若干性格差异巨大的人格。后者并不常见,甚至有学者认为心理学家的“人格分裂”是假说,文学艺术的暗示促发了这种精神疾病。被囚禁在驼轿中的尚修罗的分裂并不完全符合这两种心理疾病特征,但他的叙述确实很像精神病人的呓语。而被囚禁的种种痛苦也非常符合精神疾病的诱因。记录者经常调出来说某段失实,尚修罗的叙述真实和虚幻杂糅。
尚修罗的意识分裂成无数片,小说中另一个重要人物阿嗜尼的五官也曾各自为政,各某前途。分裂的叙述造成限制视角,组合在一起则呈现众声喧哗。有时候人的内心充满矛盾,小说人物意识的分裂隐喻了人心人性的复杂。
结语

冯玉雷先生在《阳光、土地、及发酵——关于小说艺术的对话》中自述小说创作的心路历程,冯玉雷的文学创作经历了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过度的阶段。虽然不被理解,但是作者坚持各种现代表现手法的尝试。冯玉雷一直致力于把中国传统与现代艺术技法融合的探索,《野马,尘埃》就是这种探索的成功产物。
在现实主义小说中,所有部分都为整体服务,细节好坏的评价标准就是它是否为构成了整体。冯玉雷则致力于打破这种现实主义笔法,《野马,尘埃》的很多情节与主题(整体)的关系并不鲜明,若即若离;换言之,《野马,尘埃》的主题本身就是复杂的,具有多义性。而这正是现代艺术的表现方法。
综上,“语言学”书写贯串在《野马,尘埃》的人物、结构、情节、书写方式等众多要素中,是小说主题的呈现方式。《野马,尘埃》具有谜一般的表达,读者的阅读过程就像探秘和解谜,初觉晦涩难懂,越到后来越觉得意蕴层出不穷,只有沉得住气的阅读和探索,才能有所获得。小说“只能给阅读者以关怀,唤醒被尘垢世俗蒙弊的心灵。”(《阳光、土地、及发酵》)正如作者在《后记》中说,希望年轻人静下心来,《野马,尘埃》确实达到了这种效果,促使读者学习探究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没有任何领域曾经孕育出这么多的荒谬的观念、偏见、迷梦和虚构。”35 索绪尔说这段话的意图是告诫语言学家要尽量清除这些错误,但却从另一方面道出了语言的特征。《野马,尘埃》中的语言是荒谬的,每个叙述者充满偏见,尚修罗的叙述难分幻想和真实,许多人物为了个人利益去篡改事实,随意编造。冯玉雷有意制造语言障碍,读者阅读如同闯关游戏,必须解开这些语言的谜团,才能达到意义的彼岸。
《野马,尘埃》具有前卫性,冯玉雷在吸收西方小说语言技巧的同时,与本国传统语言文化深度融合,形成了中国式的先锋性语言,《野马,尘埃》是文学语言的实验室,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了新范本。
本文首发《丝绸之路》2021年第3期,系西北师范大学华夏文明传承创新科研平台集群最新成果,中国近现代西南区域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场域视角下近代川渝历史名人研究”(XNZZSH2104)基金项目阶段成果。
作者:毛欣然,女,1984年生,成都锦城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明清近代文学、巴蜀文化。
[注 释]
1(英)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著;姜骞译:《思维的模式》[M],成都:天地出版社2019年版,第36-37页。
2、3、19、35(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3,95-105,30,13页。
4 刘赞廷: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随赵尔丰入藏戍边,在康区生活14年,编辑了如《同普县图志》《德格县图志》等大量康藏县志,编纂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刘赞廷藏稿》,为研究清末民初康藏地区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在中国藏学史上,有“清末民初康藏边地一支史笔”之称。
5 笔法:多指书法绘画上用笔的方法,在文史方面有“春秋笔法”之说。在本文中指作家写作的手法,包括文学写作的原则、方法、技巧、来源等多方面内容。)
6 马启俊:《〈庄子·逍遥游〉 “野马”注释商兑》[J],《学术界》,2015(05)。
7、8(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卷三下·应帝王第七》[M],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08,1095-1096页。
9、10、11、12、13、14、17、20、21、22、23、24、25、27、28、29、31、33、34 冯玉雷:《野马,尘埃》[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1,5-6,192,807,807,806-807,807-808,18,21,5,153,779,754,198,199,306,20-21,178,182页。
15、16(英)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金枝》[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05-506,507页。
18 罗志田:《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06)。
26 乐黛云,叶朗,倪培耕主编:《世界诗学大辞典》[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95页。
30(美)尼尔·波兹曼(NeilPostman)著;章艳译:《娱乐至死》[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5-6页。
32(汉)王充著,黄晖撰:《论衡校释·卷第五·异虚篇》[M],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21页。
本文采摘于网络,不代表本站立场,如果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