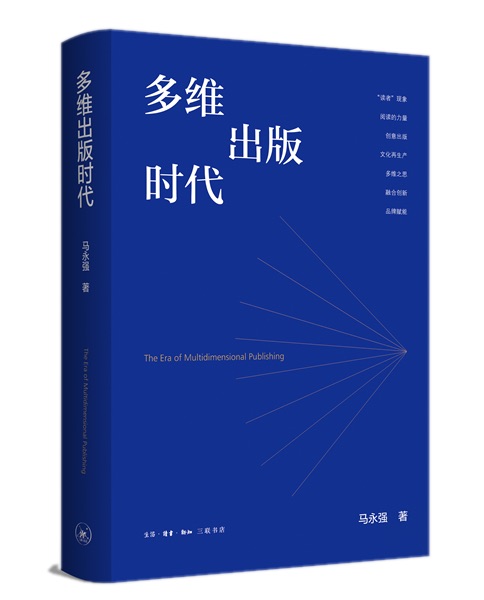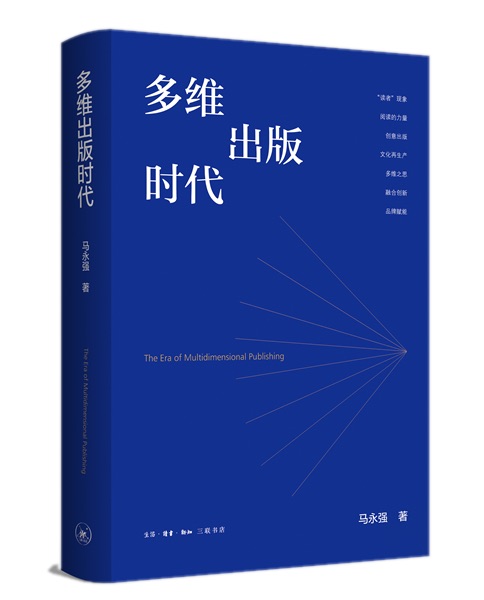作者简介
赵勇,甘肃秦安人,文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的影视改编、影视文化批评。在《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长江文艺》等刊物发表和转载多篇论文。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百年中国影视的文学改编文献整理与研究”。部分科研成果曾多次获得学术奖励。

城市疾病、日常叙事与“独立女性”悖论
——评贾平凹《暂坐》
赵 勇
内容提要:《暂坐》作为贾平凹为数不多的几部城市题材小说之一,与三十年前的小说《废都》呈现出“互文性”关系。小说以超写实的日常叙事呈现了当代城市的疾病空间,以“散点透视”的方式讲述了一群当代城市女性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焦虑,反思了“独立女性”在当下社会中构成的时代悖论。
关键词:《暂坐》;疾病空间;日常生活;“独立女性”
一、城市的疾病空间
贾平凹写城市的小说在其作品总量中占比不大,1993年创作了《废都》之后,又陆续创作了《白夜》《土门》《高兴》等几部。《暂坐》是其最新的长篇小说,也是城市题材,它与三十多年前的《废都》在文本意义上形成“互文性”关系。《废都》的故事主角是男性,通过对市场经济开展初期带有旧文人气质的知识分子的“焦点透视式”书写,呈现了知识分子在新的时代环境中的精神困境与挣扎迷失。《暂坐》则写了一群女性,对当下消费主义社会的中产阶级“独立女性”进行了“散点透视式”的书写,展现了当下女性中产阶层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焦虑。两部小说都是立足“当下”,虽然相隔三十多年,但写的都是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大的生活空间,并且都围绕“琐碎泼烦”的日常生活展开叙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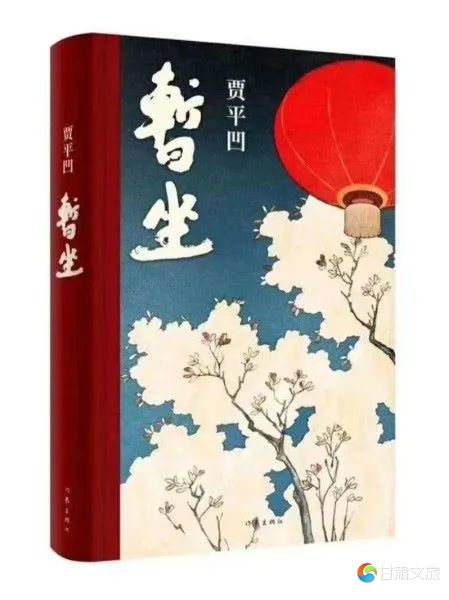
《废都》之后的近三十年间,贾平凹作品等身,但是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大多是以乡土题材为主,严格意义上的城市题材作品很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自己虽然在一直居住城市,但灵魂深处长期以来仍然是一个农村人。对于城市,尤其是当代的大城市,长期无法在心理上达到完全融入其中的状态,以至于对城市的理解不够。这有作家本人自谦的因素,但也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中国当代的其他作家,甚至其他专门作城市学术研究的学者,又有谁能说自己对当代的城市这个庞然大物有着清晰而准确的理解和认识?
相对于农村而言,城市,尤其是当代的大城市,实在太过巨大而复杂,无法用自古至今几千年以来认识农村的历史经验来套用在它上面。如果说从前的乡土社会、农村空间是单一、线性和平面化的结构,那当代的城市社会和空间则是复杂、多层次、立体式的结构。不论在文化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还是物理空间结构层面,城市的复杂程度相比农村几乎就是一个几百上千人的交响乐队和一个人弹一把琴之间的区别。但是,尽管贾平凹对城市的理解可能没有对农村的理解那么深,也并不见得他对城市的理解就不深刻。他不但对城市仍然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认识,而且在当代文学的城市写作中,形成了辨识度极高的贾氏城市书写风格。
和对农村的书写类似的是,贾平凹对城市的书写也是从“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入手。所不同的是,对于城市,作者由于自己无法在心理上完全融入城市,反过来让他获得了一部分“局外人”的疏离感,因此同样是对日常生活“琐碎泼烦”的书写,这种疏离感让贾平凹在进行城市书写时明显比农村书写显得更加轻松,尤其是《废都》和《暂坐》这两部“百分之一百”的城市题材小说(《土门》写的是城乡结合部,《高兴》的叙事对象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题材)。城市书写明显是讲“别人的”故事,而农村书写就是在讲“自己的”故事。以《暂坐》和《废都》的开头为例,《暂坐》的开头一段中这样写道:“……2016这一年,一个叫伊娃的俄罗斯女子,总感觉着她又一次到了西京,好像已经初春,雾霾却还是笼罩着整个城市。”①《废都》的开头是这样:“一千九百八十年间,西京城里出了桩异事,两个关系是死死的朋友,一日活得泼烦,去了唐贵妃杨玉环的墓地凭吊……”②这两个开头采用了同一种模式,即中国古典文学最传统的开篇方法,即:某个年代,某个地方,某个人去做某件事,从而引出故事的全篇。贾平凹的这两部书写城市的小说都是这样的开篇方式,在开篇方式上古典文学意味甚为浓厚,像是要准备平静地讲述一个遥远的故事。
而与此相对的,贾平凹在书写农村题材小说时的开篇大都有着非常强烈的自我主体代入感,而且在小说叙事上充满着“现代主义”特征,且看这几部农村题材小说的开头:
“狗尿苔怎么也不明白,他只是爬上柜盖要去墙上闻气味,木橛子上的油瓶竟然就掉了。——《古炉》③
“要我说,我最喜欢的女人还是白雪。”——《秦腔》④
“那个傍晚,在窑壁上刻下第一百七十八条道儿,乌鸦叽里咵嚓往下拉屎,顺子爹死了,我就认识了老老爷。”——《极花》⑤
“镇长戴着草帽,背包里揣了一条纸烟和三瓶矿泉水,一个人单独在全镇检查维稳和抗旱工作。”——《带灯》⑥
“子路决定了回高老庄,高老庄北五里地的稷甲岭发生了崖崩。“——《高老庄》⑦
很显然,贾平凹在《废都》之后写的农村题材小说的开篇基本都是直接进入故事的内核,这源于贾平凹对于农村题材的个人情感和主体代入感更为强烈,也基于他对于农村的认识和理解更为深刻。虽然他在城市生活的时间远远大于在农村的时间,但是对于书写城市为主体的小说,贾平凹采用的却是那种古典式的具有“间离感”的开篇方式,这种开篇方式让叙述主体中的作者从叙事中可以“抽离”出来,就如作者在在《暂坐》中后记中所说“自己变成了一只房梁上的燕子,不离人又不在人中,筑巢屋梁,万象在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暂坐》和《废都》放置在同一个维度上进行考察。

《废都》和《暂坐》的故事都是在西京城,同一个城市,也就是贾平凹生活了四十多年的那座历史悠久的古都。《废都》中的西京城和《暂坐》中的西京城,中间隔着三十年时间。在现实层面上,这近三十年间国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对于中国的任何一座省会级别的城市,在这三十年间,发展变化都是天翻地覆的。但在这两部小说中,“西京城”的城市空间形象除了多了巨大的雾霾笼罩之外,其它的方面似乎差别不大,如乱七八糟的街道、乌泱泱的人群、城中村、筒子楼、棚户区、鬼市、五花八门的地方小吃店、老城墙以及城墙上吹埙的人等,不可否认这些不像城市的城市空间景象在当下的“西京城”仍然存在,也并非“西京城”三十多年没有任何发展与进步,只是在作者眼里,这些不太唯美的城市景观才代表着这座古老城市最真实和最接地气的一面。或者可以说,这些景观是作者四十多年前初到西京城时的第一印象,也同时形成了作者在四十多年里对这座城市的“刻板印象”。
虽然《废都》和《暂坐》两部小说的开头都是先表明故事发生的公元纪年,小说中各种“历史性”的事件都显示着小说的现实感和“当下性”,但就两部小说本身对于城市的书写而言,既没有太多城市空间的外在变化,也没有现代都市精神的内在进步式的革新,在中国发展最为迅速的三十年间,贾平凹笔下的西京城,似乎有与世隔绝之感。然而,在《废都》和《暂坐》中,虽然现代都市精神缺乏,“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支配”及“市场准入和民主参与”⑧都鲜有表现,但作为现代城市飞速发展的“城市病”则一样不缺,而且在贾平凹细网打捞式的书写下,城市病中所有的症状都像海底潜伏的垃圾一样全部被网出水面。城市有疾病,人也有疾病,《暂坐》的故事也是以夏自花这个白血病人生病住院直到离世为线索贯穿起来的,小说中夏自花的病在身体上,其他人的病则在精神上,城市的疾病则从外到内到处都是。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从鲁迅算起,有着太多的疾病叙事。如果说鲁迅的疾病叙事是对那个时代落后愚昧的社会的批判,贾平凹的疾病叙事同样也是对当下时代社会的隐喻。人的疾病隐喻城市的疾病,隐喻时代的疾病,人的血液出了问题,城市的血液也同样出了问题,《暂坐》中的疾病叙事正是一种“疾病的隐喻”,城乡区隔,阶层区隔,雾霾污染,空间虚浮肿胀、精神萎缩颓败,上层精英的空虚,中产阶层的焦虑、底层民众的麻木,这些“疾病”共同侵蚀着城市空间。在鲁迅的《药》中,华小栓吃了人血馒头的“药”也没能痊愈,《明天》中的宝儿吃了“婴儿保命丸”很快就死了。《暂坐》中夏自花虽然可以享受现代医院的科学治疗和朋友们的精心照顾,还很幸运地匹配到了高文来的血小板,但终究仍然没能挽回性命。鲁迅借小说批判社会的黑暗,不存任何幻想,在小说《药》中,最后墓地树枝上的乌鸦终究没有飞到坟头上来,《明天》中的单四嫂子也没能做到见儿子的梦。《废都》中庄之蝶无法忍受抑郁,最后选择了悲剧式的出走,而《暂坐》中夏自花的病没能治好,冯迎意外地死去,活佛也没能等到,但小说中陆以可死去的父亲两次出现,冯迎的幽灵回来捎话,在绝望的尽头通过“反魅”叙事构建出了一个给人些许“安慰”和“幻想”的反技术理性的空间。
不论是《废都》中的城市空间,还是《暂坐》中的城市空间,都与主流媒体宣传的现代城市形象截然不同,这是文学意义上的“西京城”,更是主旋律话语之外可能更加真实的“西京城”。在这里,公共秩序的混乱,边缘空间颓败,阶层圈子区隔,资本权力傲慢,这些城市空间疾病随着小说中故事展开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
在现代城市里,时间的计量精准,意义明确,但在生命意义上往往却沦为一个空洞的能指,没有附着自然和生命的鲜活意义。现代城市里的时间只是一个和价值利益对应的数字符号,它在无情地度量着生命的金钱价值的同时将生命切割成一条条一缕缕的碎片。正如《废都》和《暂坐》两部小说开头就立即标明的年份只是交代出一个宏大而虚空的时代背景而已,不论是《废都》中“公元一千九百八十年的西京城”,还是在《暂坐》中“2016年的西京城”里,全然没有诗意的栖居,不论是在庄之蝶的“求缺屋”还是弈光的“拾云堂”,以及海若的“暂坐”茶庄里,他们都没能摆脱“无历史”“无主体”“伪实践”⑨的“泼烦”生活。这种生活是从城市的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再到下一个空间,是从茶楼到大街上,从西涝里到拾云堂,从西明医院到火锅店,从建业街到丰登巷,从香格里拉饭店到筒子楼,从泡沫馆到能量舱馆,从咖啡吧到麻将馆,从城中村到停车场……生活就是在这许多的空间中来回切换。
传统的农村生活是跟着“节气”走的,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日出而做日落而息,虽然近几十年以来随着城市的剧烈扩张导致农村日渐凋蔽,但时间在农村仍然没有完全丧失生命意义。而在现代化的城市里,时间已经完全同生命割裂开来,各种事件密密麻麻目不暇接热闹非凡,但过后一切都像从未发生过,像一场梦境,有种令人迷幻的不真实感,就像《废都》开头天空中出现了四个太阳,《暂坐》开头描绘的铺天盖地的雾霾,都营造出了这种迷幻而不真实的感觉。城市空间的迷幻,日常生活的芜杂、泼烦,让身在其中的个体焦虑不安,为了寻找意义,《废都》中的主人公庄之蝶去古墓凭吊,到城墙上吹埙,经常在家里一个人播放的哀乐,沉迷于和不同女人的性爱,然而最终仍然没有寻找到真正的意义,《暂坐》中的茶庄女老板海若一直在等待活佛,试图通过“皈依”获得心灵的寄托,同时全力以赴地积攒“功德”,为自己 的闺蜜们解决一件又一件的琐事,最终仍然是活佛没等到,闺蜜们却“死、走、伤、离、散”。
社会极速发展的结果是不同阶层的财富差异越来越大,而且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彼此之间失去了沟通的渠道,逐渐成为了不同世界的人。就像在郝景芳的科幻小说《北京折叠》中描述的一样,不同阶层处在不同的折叠层,互相排斥,拒绝流通。西京城也不能例外,在现实层面上,上层社会的西京城,和底层社会的西京城也不在一个空间维度里,而《暂坐》恰好要书写一群上流社会的人,为了避免“不接地气”,作者在小说中有意让“十玉”们时常步行着从一个城市空间到另一个城市空间,各种底层化的景象就在我们眼前依次展开。海若去找陆以可,电梯坏了,麻木的工人们白眼瞪人,讨债的农民工每天在饭馆里只点米饭不点菜,医院门口饭馆里农村妇女直接往桌子下面的垃圾桶里吐痰,停车场大爷经常怒斥摆摊的穷人。底层仍然是穷苦不堪,素质低下,而且相互倾轧。作者在此通过小说作出反思,社会经济有了那么巨大的发展,为何这些底层的人仍然是“穷极了的”。小说在这里着眼上层社会的书写时同时呈现出底层的生存状态,阶层固化、信仰共同体消失,上层社会的虚伪和底层社会的麻木,阶层间的区隔,这难道就是三十年社会快速发展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小说的叙事有了“政治性”的意味。
二、“超写实”的日常生活叙事
在《暂坐》中,作者把叙事交给了芜杂的日常生活本身,让小说的叙事在日常生活的这些琐碎里自己流动,虽然这种流动会让叙事显得迟缓、凝涩、滞重,但恰是在这种迟缓、凝涩、滞重中刻画出了日常生活的原生态和本真状态,这种状态让人有强烈的代入感,甚至比真实的现实更加“真实”。这种本真状态不是纯粹的文学想象,也不是单纯地剪辑和拼接,而是对真实日常生活近乎百分百的还原,是对日常生活景观微毫毕见的“超级写实性”的书写,这种超写实的书写深刻地揭示了日常现实的结构和肌理。

在《暂坐》第一章中,对暂坐茶庄尤其是二楼佛堂的描写细到发毫,对佛堂的东西南北四面墙上壁画内容的介绍,更是多达近七百字。第三章里海若和伊娃来到西涝里的棚户区找陆以可,来到巷道北头的楼前时这样写道:“楼前是个喷水池,却没有水,池子里落着厚厚的尘土。”此时完全可以直接写海若和伊娃上楼,但在此处却插入了两段楼下的日常生活景象:
“(喷水池)旁边是栽了几种健身器材,两个人双手挂在单杠上,一动不动,像是在吊死。一个人则将脊梁不停地撞篮球架的铁柱子,咚咚,一只鸽子飞来要歇脚,又飞走了。有了二胡响,循声寻去,有人就坐在远处的砖磊子上,低着头,看不清眉眼,把悲风中得来的音调变成了一种哀伤,可能是常在那里拉,也没听众。”⑩
这样的内容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原本习以为常的、无聊乏味的日常生活景象在这种“长镜头”的捕捉下显示出一种怪诞和荒谬之美。而小说中当海若和陆以可才开始准备上陆以可居住的楼,又遇上电梯坏了,两个“浑身油污”的工人蹲在下边正在修理,问了两次没得到任何回答,只收到了工人的一个白眼。在两个工人眼里,眼前两位瞧打扮肯定是中上流人士,和自己压根不是同一世界的人,所以懒得理会。就这一个“没回应”和白眼,就写出了城市日常中的阶层区隔,城市的光亮部分和阴影部分互相隔离,毫不相关。
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沉淀在人们心里的文化基因并不是通过城市化的外在革新就能改变,虽然外在的变革能带动人内心观念的改变,但绝不是几十年的经济突飞猛进就可以让所有人彻底“洗心革面”,城市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和许多行为方式,仍然存留着几千年农业文化的烙印,这也是为什么在贾平凹笔下的城市“不像”城市,其实这才是最真实的城市,至少是最真实的城市面孔之一,而我们在大多数语境中言及的城市则是建立在官宣和想象美化后的城市。现代城市的核心特征一般而言都认为是时尚、发达、快节奏、繁华等,但这些特征其实都仅仅是相对的概念,就如“西京城”相对“陕南山区”自然是时尚、发达、快节奏、繁华的,但如果和更加发达的“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比较,它就又变成了土气、落后、慢节奏、偏僻,所以城市的现代感、时尚感、繁华感、节奏感等并不能被某个日常景象准确地证明,这种先验式的定义方式不仅不可靠,而且会在人内心产生出一种迷幻和虚无之感,《暂坐》中对于许多老城区和街道的原生态式的描写就让觉得真实可信,而先验式地定义一种或几种城市的普遍特征或者用一些常见的技术和文化符号表现城市则很难让人产生真正的共鸣。
城市的现代感、时尚感、繁华感等在贾平凹书写城市的两部小说中很少见到,反而脏乱差、秩序混乱、人像没头的苍蝇等倒经常是贾平凹书写城市小说中最多的景像,这样的城市看起来很不想现代化的大城市,倒像落后的城乡结合部。其实,我们印象中的城市往往是对不好看的那些场景实施了有意或无意地“清场”,留下的只是经过过滤后可以“上得了台面”的景观,而这些景观只是城市的表象,或者说一部分景象,而那些不好看的“上不了台面”景象仍然真实地存在,只是不再为人所关注和书写,被人选择性地无视,被宣传者选择性地排除,被书写者选择性地过滤,不但在许多记录这个时代的文本中不出现,甚至在人们的记忆中也被永久地删除。
贾平凹极为擅长书写市井烟火气息浓厚的日常景象,从日常生活琐碎细节着手,一针一线看似随意实则绵密,织起来一幅当代城市社会的真实图景。还原出生活的真实来,不但还原出来,而且还要通过“超写实”的描写狠狠地强调这种真实,这是一种文学书写技术的回归,回归到文学最开始的状态,这也是一种反讽,对遮蔽、粉饰、美化、自大、虚伪的反讽,让生活在日常琐碎中显出原形。在《废都》之后的小说中,这中叙事方式几乎是贾平凹小说的“标配”。《暂坐》沿袭了这种写法,这种超写实主义虽带有机械复制的批判意味,但并非是机械的描绘客体,而是在写实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加强了表现对象的客观性,用一种摄影师的视角进行描绘,不脱离底层生活,烟火气息浓厚。
如《暂坐》中写司一楠在兴隆街一段中,切肉的人耳朵上偏偏要夹一支烟,外卖骑手倒地后都是先查看饭菜是否溢出,卖干果的红枣时常会被人顺走一颗,买下熟肉的人边买边用手撕下一块嚼,还有陆以可去西涝里时,看见老太太给小孩擤鼻涕,辛起和伊娃住在城中村时夜晚听到的叫床声景象的细致描写等,这种描写生动细腻,这是小说中司一楠或者陆以可看见的真实场景,并非是作者的全知视角,这种一如摄像机跟着人物行走式的写法让故事情节的节奏缓慢,只能一帧一帧地徐徐推进。这种超写实的书写貌似如实记录,未经加工,实则不然,只是加工得不着痕迹,像超写实的画,似乎和摄影一样,然而仍然有艺术的各种强调和表现在其中,并不仅仅以还原日常生活的本身为最终目的,而是在这种超写实的还原中拓展着小说中日常生活的叙事空间。
从《废都》到《暂坐》,贾平凹城市题材小说总能以城市“日常生活流”的叙事抓住“当下”的脉搏,去除本质化、理性化、神圣化的先在判断,果断还原生活的原生态,利用自己独特的细腻书写构建出“小”时代的日常观感。贾平凹小说文本中总会有许多密实而鲜活的生活细节,在别人可能会一笔带过的地方,他经常会在一个细节驻笔很久,围绕这个细节进行进一步的强调,随意地在一个点上作“无意义”地生发,在理性意义上没什么可写的地方继续书写,这在某种程度上和写实的极限,不断拓展写实的边界,在不能突破之处继续推进。《暂坐》中写饭馆门前的苍蝇,一定要说明苍蝇是不是绿头的。茶庄的小唐往车上扔废弃的花束,会详细描写扔花时的动作,两条腿分别是什么姿态。这并不是“讲故事”,而是用虚构的文本记录最真实细致的生活状态。
贾平凹的小说中的大量“原生态”的场景不但没有“美图”感,也没有“滤镜”感,他甚至会用显微镜扫描到所有的犄角旮旯,把那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全都展示出来。这种写法几乎见于贾平凹所有的小说当中,尤其是《废都》之后的小说中,我们会看到许多熟悉的“脏段子”,比如《废都》中设计公共厕所的女设计师上公厕时需要事先拿两块砖头的尴尬,《山本》井宗秀父亲喝醉后中掉进臭气熏天的茅坑淹死,《古炉》中每隔各种几页都会出现的排泄物,各种“砸屎”的场景,《怀念狼》中充斥的各种人物的“兽欲”,《高老庄》中对高子路和西夏性事不厌其烦地书写……即便是《暂坐》这样的书写都市中上层社会“优游尊贵”的女性小说,仍然不时地要把视角引向一些“脏乱差”的地方,比如关于“鼻涕擤一池塘”,城中村夜晚的叫床声等。这种有意识地对小说文本的“污化”和许多熟悉的贾氏“段子”的重复出现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会让读者产生阅读厌恶感,但这些场景在生活中其实都司空见惯,只是在许多作家笔下被过滤掉了,而在贾平凹这里,这些书写却实实在在地形成了一种粗俗而有力解构风格,在超写实中不断地解构,解构了崇高严肃高贵和虚伪,解构了历史,解构了社会,解构了文化,甚至解构了马克思社会属性意义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后现代”书写,也是具有“政治性”意义的书写。

除了超写实之外,小说故事的偶然性也指向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暂坐》的故事结构虽然套用了一个梦境的“壳子”,就像“本故事纯属虚构”的开场白一样,明确告诉你这是小说,当不得真,但其实这只是“虚晃一枪”而已,这个“壳子”才是真正的“当不得真”,壳子里面包裹的恰是日常生活的真相。日常生活本身就是由许多偶然性事件组成的,它并没有事先设计好的开端和结局。正如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中所指出的,日常生活具有“多面性、流动性、含糊性、易变性”。?小说《暂坐》正像是这种具有“多面性、流动性、含糊性、易变性”生活琐事的日常记录,叙事流向哪里,似乎不受作者控制,而是任由人物的日常生活本身原生态地流动。
在小说《暂坐》中,偶然性和随机性转折随处可见。比如作为串起整个故事线索人的夏自花,在她的病似乎即将好转时,却突然地死去了。夏自花死后,她的情人“姓曾的”浮出水面,按正常的戏剧化想象,此时应该有一个戏剧化的高潮,围绕夏磊的抚养权展开争夺,结果“姓曾的”以一个陆以可的“再生父亲”形象的出现让这个冲突还没开始就平淡地结束。应丽后雇佣讨债公司的章怀去讨债,也是冲突还没激化时就突然停止了。辛起的前男友大闹茶庄,在“闹出人命”前警察及时出现。茶庄爆炸,海若被有关部门带走,整个故事原本可以借此进入一个更有故事性和趣味性的阶段,但作者在此却突然留白收尾,对于“西京十玉”何去何从,也并不做交待。这不符合普通的小说阅读习惯,但却符合日常生活的真实逻辑,并不强调戏剧化,而是适时地遏制戏剧化情节的扩张,刻意不产生过度夸张和戏剧性的情节。诚然,现实的日常生活中肯定有许多可能比这要离奇有趣的情节,但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都是庸常而琐碎的状态,并没有多少戏剧化,作为小说《暂坐》,对故事情节的发展也总是“点到为止”,绝不刻意扩张。
三、“独立女性”的悖论
《暂坐》中对当代城市的“独立女性”的书写力图展示出了她们美好向上的一面,的确写出了他们的“精英感”。她们大多数身家不菲,气质不凡,精于化妆打扮,注重生活品质,她们是让大部分普通阶层的人艳羡的一个群体,小说对“西京十玉”的叙事整体也呈现出一种音乐性的美感。《暂坐》开篇以一个外国留学生伊娃的视角展开,缓慢而细密,就像一把板胡在拉一首慢板的秦腔牌子曲,到了“西京十玉”齐聚茶庄,则是花音快板鸣奏,也像是几十把琵琶协奏的《霓裳羽衣曲》,到了众人轮流照顾夏自花住医院,则转为了苦音,应丽后和严念初反目,雇佣讨债公司去要账,故事的调子又转为箭板,高亢而激越,至于司一楠和徐栖之间暧昧的同性恋关系,则是变成花音慢板,到了最后海若被纪委带走,夏自花去世,冯迎的死讯传来,茶庄爆炸,恰似锣鼓铜器奏出的连续急促的打击乐重击,也像一条在平摊上流淌的河水骤然间遇到几个大的沟坎,然后猛然间从万丈悬崖跌下,“四弦一声如裂帛”一切戛然而止,余音绕梁。
和《废都》以男性为中心不同,《暂坐》则主要写女性,不是一个,而是一群。也不是以其中的一位为主角重点书写,而是十余个女性平均着墨。《废都》中包括小说主人公庄之蝶在内的西京城“四大名人”都是男性,他们周围的女人,大多是他们的陪衬和玩物。而《暂坐》中的这些女性都属于这个城市和这个时代的上流人物,中产阶层,她们经济优渥、打扮时尚,有着当代城市中产阶层事业型女性的自信和贵态,但在小说中对她们“霓裳羽衣曲”式的华丽书写背后,作者无声无息地揭示了“独立女性”在当下社会的时代悖论。在这些“独立女性”强势的外表下,却大多都情感细腻而脆弱,像玻璃水晶一样一碰即碎,内心深处又各有各的挣扎与迷茫。她们一面坚持精神独立经济独立,却一面仍然不得不依附于男权,她们关心别人的痛苦,却隐瞒自己的脆弱,刚强自负不能容忍居于人后,但又儿女情长感情脆弱。貌似精神独立,实则“风吹风也累,花开花也疼”,脆弱得“一个指头都可以戳倒”。
《暂坐》中的主要男性角色是作家弈光,但是小说中“西京十玉”的女性圈子里,弈光这个男性仍是她们的主角,她们的许多事情仍然需要依赖于这个男性来解决。“独立女性”显然无法完全“独立”。弈光身上有着太多《废都》中庄之蝶的影子。《废都》中庄之蝶最后选择“出走”,而且似乎是死在了车站,这是三十年前旧文人式的知识分子在时代漩涡中,心理挣扎、扭曲最后绝望的悲剧式结局,但是经历了三十年的时代洗礼,这类人逐渐适应了新的时代,他“活过来了”。弈光在《暂坐》中比庄之蝶活得“明白”和“通透”,他清楚自己的定位,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知道在当今这个时代,像他这样的文化“名人”,论手中权力比不上政府官员,论经济实力比不上大小老板,论名气热度比不上娱乐明星,自己只不过是城市社会中权力和资本夹缝中一个“附生物”,所以在他的内心深处并无知识分子文人面对权力和利益时的佯装清高,也无男女关系问题上的道德纠结,他可以熟练而大方地收受商人的10万元写一幅书法,也可以经常和不同的年轻女孩睡觉,全然没有《废都》中庄之蝶的内心矛盾和挣扎。这是时代的进步抑或退步不易下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商品市场经济刚刚展开,文人知识分子在利益面前还有些羞涩扭捏,而到了今天,似乎一切都被明明白白地定价,对社会的各种明暗法则“从了”之后的“弈光”们,活得轻松而自在,可以游刃有余地穿梭在政府领导、商人老板、以及中产阶层的精英女性圈子里。

《暂坐》由俄罗斯留学生伊娃的视角陆续引出“西京十玉”,第一个出场的是海若,暂坐茶庄老板,“闺蜜团”的召集人,性子急,心肠热,慷慨,重情义,是他们的“大姐”。海若在小说中的出场值得一说,先是伊娃来到茶庄,海若不在,四个店员小唐小苏小甄还有张嫂先行亮相,然后一个声音才从楼下传来:“活佛没到,伊娃倒先来了”,《红楼梦》中王熙凤的出场正是这样,“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在这里海若的出场方式更像中国传统戏曲中的大人物出场,先是四个小兵、龙套、或者丫鬟出来走场、铺垫、亮相、分列两厢,然后后台一声叫板,主角才款款登场亮相,这种主角式的铺垫实则为反衬后面海若的脆弱情感和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海若精干强势而心地善良,却婚姻不幸,于是更看重闺蜜们关系的维护,小说从头到尾,她就从没有清闲过,并不是忙于茶庄的经营,而是忙于处理闺蜜们的各种杂事。夏自花白血病住院,她不但安排闺蜜们轮流值班照顾,还要帮忙联系血小板,找人调换病房,以及照料夏的老母亲和小儿子。夏自花去世,她不但全面主持安排丧葬事宜,而且还要为了处理好夏的老母亲和小儿子善后安置,去和夏的情人“姓曾的”谈判。闺蜜应丽后由严念初介绍放贷被骗钱,她不但要亲自出马去和人周旋讨债,还要从中协调应丽后和严念初的关系,维持“闺蜜团”的稳定。海若对朋友如此尽心尽力,确实可当得起一个义字当头巾帼不让须眉的“大姐”,。然而,在自己的婚姻和家庭方面,她又是一个十足的弱者,婚姻不幸,儿子叛逆,自己有好感的弈光,最后也让她大失所望。她曾经在心里自我安慰,想着弈光宁肯和那些年轻的女孩有染,也不和她发生关系,是因为弈光不想打破他们这种和谐的亲密朋友状态,但真正的事实很可能是:在男人眼里,她已经老了,在身体层面上已经对弈光这样的男人失去了魅惑力。闺蜜中最是打着“独立女性”旗帜的“女强人”海若,在精神焦虑的深夜接到弈光电话后,要换上一套性感的黑色内衣去赴约。陆亦可为了得到一块机场的广告牌需要精心打扮找柳局长,违心地陪“油腻大叔”范伯生吃饭,陪前男友徐少林吃饭,严念初为了医疗器材生意整天缠着西明医院的王院长,辛起委身香港富商想实现阶层跨越结果最后发现被骗,她们都一样不得不利用自己的性别和身体获得红利,也就是说,她们仍然要通过“诱惑”去把握男人,进而把握世界。即便是她们经常聚会得以暂时获得温暖和安全感的茶楼,也不过是权力的赏赐,是海若找市政府领导的关系低价租来的。而在她们这群光鲜亮丽的女性精英们中间,老男人弈光仍然是他们聚会的主角。海若在深夜换上性感内衣到拾云堂赴约时,却发现弈光家里还有其他人,弈光要和她说的是冯迎死去的消息,那一刻对于海若的心灵来说是双重的打击。
对于“闺蜜团”的姐妹们,海若是真诚的,对于男性,对于这个社会的深层法则,不光是海若,闺蜜团的其他人也一样,都仍然缺乏准确的理解和认识。“独立女性”在此变成了一个她们既在坚持又在背弃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小说《暂坐》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这样一种悖论,因为女性的真正独立不只是经济上的独立,还要有情感上的自我操控,但这并不是要和男性对立或者决裂,而是在情感、婚姻、家庭、事业、生活构建中作为和男性对等的角色出现。但是在当下的社会,即便是取得了经济独立的“西京十玉”们,仍然无法真正实现“独立”,资本和传统男权文化仍然在不谋而合且相互推波助澜,女性仍然在被“物化”。《暂坐》中的这些“独立女性”,虽然经济实力优渥,但大多仍然无法逃脱情感上的悲剧命运。最后当茶庄意外发生煤气爆炸,海若却因低价租用茶庄楼层牵涉相关领导腐败而被纪委带走,她的结局如何小说并未明言,但可以估计大概也是凶多吉少。这并非是作者要宣扬好人没有好报的负能量,而是生为女性,时至今日也没有真正走出男权社会密不透风的恢恢巨网,女性要获得经济独立,就要服从社会规则和男权的规训,而一旦服从了这种规则和规训,精神独立就根本无从谈起,这恰是“独立女性”的时代悖论。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参考文献
①⑩贾平凹:《暂坐》,《当代》2020年第3期。
②贾平凹:《废都》,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③贾平凹:《古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④贾平凹:《秦腔》,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⑤贾平凹:《极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⑥贾平凹:《带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⑦贾平凹:《高老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⑧吴琳:《从现代城市兴起探寻现代都市精神》,《湖北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⑨李宝文:《如何展开日常生活批判:科西克关于日常生活批判的四重维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6期。
⑩刘怀玉:《列斐伏尔与20世纪西方的几种日常生活批判倾向》,《求是学刊》2003年第5期。
来源:现代文学史料
本文采摘于网络,不代表本站立场,如果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