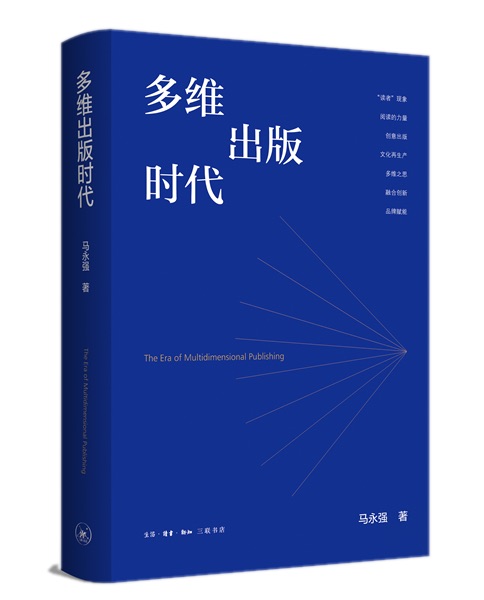丝绸之路西行文献是研究中国西北地区历史文化和文学的珍贵资料。以文献形式而言,由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两部分组成。其中,出土文献以简牍、敦煌文书和吐鲁番文书中的西行资料为主,传世文献则以西行记为主。丝绸之路行记文献是丝绸之路西行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代表性文体。所谓“行记”,即“行程记”的省称,又名行纪、行传、纪行、纪事、行略、行录、游记等,或冠以日记、志等名称。行记文献大多独立成书,并按时序记录旅程见闻,融记叙、描写、考辩、议论等内容为一体,一般具备时间和事件两个写作维度。写法上通常用第一或第三人称,或叙事,或写人,或写景,或抒情,兼具人物传记和游记文体的特征。
一、丝绸之路行记文献的流变及研究范围
目前发现的丝绸之路出土西行文献中最早、最著名的应当是汉简里程简,一枚出土于居延,称居延里程简,详细记载了从长安出发到敦煌,再到居延地区的通行驿置名称以及各地之间的具体里程;一枚出土于敦煌悬泉,称悬泉里程简,记载东起仓松,经鸾鸟、小张掖、姑臧、显美、觻得、昭武、祁连、表是、玉门、沙头、乾齐到渊泉的行经路线。当然,汉简中间接记载和反映西行路线的资料还有不少。丝绸之路出土文献中最主要的是吐鲁番文书和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中作为行记性质的文书并不多,但是记载行程内容的资料弥足珍贵,如《石染典过所》等。敦煌文献中关于行记的记载很多,如S.2009《西州图经》、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大唐西域记》的几种抄本、S.383《西天路竟一本》、P.3532《慧超往五天竺国行记》、S.529《诸山圣迹志》、杏雨书屋藏羽032《沙州专使往五台山行记》、P.2977《五台山志残卷》、P.4648《往五台山行记》、S.397《往五台山行记》、P.3973《往五台山行记》、P.3931《印度普化大师游五台山行记》等,这些珍贵的出土文献对揭示当时中外交通行程路线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学界研究已多,此不赘述。传世西行文献中最早的应当是《山海经》和《穆天子传》,此类著述虽为较早的记“行”文献,但并非丝绸之路西行纪行的专书。

行记之名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隋书·经籍志》就著录有《魏聘使行记》《封君义行记》《李谐行记》等直接以“行记”命名的作品。完整的“行记”当起源于汉魏,这与丝绸之路的开通密不可分。如张骞“凿空”西域后,撰写的《张骞出关志》是我国现存第一部记录西域人文风俗的著作,后汉班勇的《西域风土记》等均属此类著作。
另外,从《史记》《汉书》《后汉书》《隋书》等史书可知,这一时期还出现过《西国行记》《天竺行记》《天竺行传》等行记作品。这些行记虽多亡佚,但从其佚文推断,多载西域物产、风俗等,已具备西行记的内容特征。因汉代为行记创作的萌芽阶段,行记文体的写法还在探索过程中,故虽标为行记,却不具备行记文体的明显特征。后人发展了这一文体,多以传记形式记录完整的旅行经历,这成为六朝行传的典型特征。六朝时期为行记的诞生时期,晋宋间出现了大批西行求法的僧人,僧人求法回国后,多撰书纪行,如《法显传》(又名《法显行传》或《佛国记》)。北魏僧人慧生所撰的行记亦名《慧生行传》。根据保存比较完整的《法显传》《宋云行记》所载可知,二书均以人物活动为中心,以人物行踪为线索,按时间顺序连续叙述人物的西行行程,而当时的正史人物传也以叙述人物一生行实为主,二者性质接近,故名之曰传。因这类行记大量涉及舆地,故后人多将这类著述归于地理志。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来看,晋宋僧人的求法传记多以人物活动为中心,内容虽涉及舆地,却多以交代行程为重点,叙述方式具有明显的叙事性。除了僧人撰写行记外,文人也开始撰写各种行役记,主要记述的是六朝文人从驾、出征等公行和私行,代表性的文人行记有郭缘生的《述征记》和《续述征记》。这类作品不同于僧人的求法行记,它没有完整的人物行程经历,内容和结构都是松散的,记录行程不是它的首要任务,笔墨多着重于山川风土的记录上,后人将这类作品归入山水游记。李德辉先生通过论证,认为这类散文其实是六朝行记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因为在山川记录后面,隐藏着“行人”及其行踪,故应该将这类杂记散文归入行记散文。
隋唐时期,国力强盛,丝绸之路空前活跃,中央政府与西域往来频繁,丝绸之路上行人不断,产生了大量的西北行记著作。根据现存资料统计,隋有行记文献6种,唐有15种。西北行记在隋唐时期进入创作的成熟阶段。唐代行记种类增多,除僧人求法行记外,还有外国使臣行记、文臣行记及综述体行记等。到了宋元明时期,从全国范围看,行记的数量与种类较唐及五代有所增加,但由于战争等因素的影响,西北行记著作明显减少,是西北行记创作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僧人行记数量开始减少,域外行记、文臣行记和综述体行记数量有所增加,行记的文学性大大增强,并且出现新的行记体式——日记体行记。到了清代,西北行记创作进入繁荣时期,其中有一类作者值得高度关注。清朝统治的268年中,有大量的贬谪文人被发配到西北边疆地区戍边。这些流放文人继承了行记撰写的传统,在边疆工作生活的过程中,注重记录边疆地区的生活风俗以及自然风光,创作了大量的西行记著作。到了近代,边疆危机进一步加深,大批有识之士将目光转移到西北和西南边疆地区,他们到边疆地区调研考察,并记述旅途见闻,写作行记,为后世研究近代边疆历史文化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20世纪初,敦煌和西域文书的发现以及交通条件的改善,吸引了大批文人学者到西部旅行和考察,他们创作了大量的西行记,西行记的创作进入鼎盛期。在这些西行记中,饱含着作家难能可贵的忧患意识。至于现代作家创作的西行记,则视野更加宽广,表达方法更为多样,多方面展示西北独特的风貌。这些行记作品多融情于景,又极力揭露当时西北一带政治的腐败、官僚的丑恶和自然灾害带给百姓的祸患,具有重要的文献和文学价值。
行记文献是丝绸之路西行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流变,目前可考的西北行记著作有200多种,为后世学者研究西北地区历史文化提供了第一手宝贵的文献资料。
二、丝绸之路行记文献的认识意义
丝绸之路行记文献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从多角度反映了西北地区的自然状况和社会风貌。西北地区不同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文学、军事、民俗、天文地理、山川物产等内容都在丝绸之路行记文献中得到载录,通过行记文献可以认识西部人文与自然景观,充分了解西北社会的发展与变化。

(一)丝绸之路行记文献反映了西北交通发展的真实状况
行记主要依据行程路线中的所见所闻来纪行,故丝绸之路行记文献中有大量反映西北交通的作品。如据《法显传》记载,法显西行路线国内段大致为长安-陇县-榆中-乐都-张掖-敦煌-西域,法显从西安出发,到今甘肃境内后,其路线与丝绸之路甘肃段南线基本吻合。洪亮吉《伊犁日记》中记载的西行线路为:北京-涿州-山西榆次-曲沃-蒲州(运城)-陕西潼关-临潼-西安府-咸阳-乾州-邠州(今陕西彬县)-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平凉府-隆德-静宁-会宁-安定(今定西)-金县(今榆中)-兰州-平番(今永登)-古浪-凉州(今武威)-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安西-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惠远城(伊犁将军驻地),可见洪亮吉的西行路线与丝绸之路的北线基本吻合。综观历代丝绸之路行记文献,我们不难发现行记创作者的西行路线与丝绸之路路线的发展几乎同步。随着时代的发展,西行线路更多,西行里程也更远。
上世纪初,随着公路、铁路、航空等现代交通运输方式出现,西北的交通状况显著改善。民国时期,大量学者借助火车、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到达西北地区,这些变化都在西行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如刘文海就曾乘火车和汽车从南京到达西安,顾颉刚则乘坐飞机从西安到兰州,侯鸿鉴又从兰州飞往西宁。所有这些无疑都展现了西北交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二)丝绸之路行记文献载录了西北地区富饶的物产
西北地区历来以物产丰富著称,不仅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丰富,作物品种众多,而且质量上乘,所有这些物产在西行文献里都有充分的反映。我们仅以《西北视察记》为例进行简要梳理,即可见一斑。陈赓雅《西北视察记》记载了产自甘肃省内的十余种矿物,他指出甘肃矿产“蕴藏丰富,已被调查确实,并间有经人开采者:一曰金矿,产地为敦煌、酒泉……成县等。二曰银矿,产地为山丹、永登……两当等。三曰水银,产地为文县、武都等。四曰石油,产地为玉门、酒泉、敦煌等。五曰煤矿,分布各地,几遍全省……六曰盐矿,敦煌、高台、民勤……西和等县均产之。七曰铜矿,皋兰……玉门等县均产之。八曰铁矿,永登、古浪、会宁、成县、两当、岷县、临潭均产之。九曰铅矿,永登、武威、靖远、岷、成等县均产之。十曰石棉,武威、永昌、华亭、天水等县均产之。此外皋兰、永登等县,尚产锰矿。”西北的有色金属、石油、煤矿等至今仍在开采,是当地重要的生产部门。
据西行文献记载,西北地区不仅生产丰富的毛皮、药材、木材,还种植小麦、水稻、瓜果、蔬菜等作物。这些物产,沿着丝绸之路流通,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见证和纽带。
(三)丝绸之路行记文献反映了西北地区的社会问题
西北地区有着独特的社会历史环境,西行文献中有大量反映当时西北地区社会问题的内容。如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中提到的鸦片问题。西北各省当时大量种植鸦片,最著者有武威、张掖、敦煌等地。据范长江记载:“酒泉和张掖一样,农民最大的出产,全靠鸦片。酒、张两处的烟土,不及武威的好,武威鸦片销山西,供晋人吸食之用。酒泉鸦片走平津,以为造‘白面’的原料。”可见,自鸦片战争以后,鸦片种植在西北地区泛滥,严重危害西北地区的社会稳定。另外,西北自古为多民族地区,在19世纪后半期,这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民族争端不断。陶保廉《辛卯侍行记》中就记载了大量的民族问题,如“窃意汉回相仇,匪伊朝夕,睚眦细故,积小成大”;又如洮州土司“鱼肉其民,莫敢控告。地僻官远,驾驭甚艰”,等等。他认为西北的民族问题不仅是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而且涉及到政府与少数民族的矛盾,宗教教派间的矛盾等。西北民族问题一直持续到民国,范长江和顾颉刚在其行记著作中也关注到这一问题,探讨过矛盾的根源,但仍然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积极有效的民族政策,才彻底解决了这一矛盾。
西行者们经过实地调研后多将鸦片问题和民族问题归结于西北政治的腐败,政治的腐败投射在文化领域就是教育的落后。具有忧患意识的文人,在寻求西北的出路时,将目光投向了教育,民国时的行记文献中记载了大量关于西北教育的内容。如林鹏侠的《西北行》记录了当时兰州的教育状况,发出了西北教育“程度均甚低,不能与内地比较”的感慨,并指出:“国家之强弱,惟视教育之兴衰以为正比例。甘省当西北边防要冲,国民教育,尤属不可缓图。”在这里,林鹏侠认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运动同发展西北教育密不可分,西北只有在文化经济上享有同等的发展机会,才能真正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社会的稳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的解放。
除上述认识价值外,现存丝绸之路行记文献中尚有大量篇幅描写西北风俗、经济发展、宗教文化、刑律制度、历史沿革、建筑风格、饮食衣饰、气候地理、生态环境等内容,为我们认识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状况提供了多个角度,也为我们展现出特定时代西北地区的全景风貌。
三、丝绸之路行记文献的文学价值
丝绸之路行记文献历史悠久,创作丰富,是中国文学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丝绸之路行记文献的创作使西部和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中国文学的想象空间得以向西拓展,同时也为中国文学地图的重绘和文学研究新视野的开拓提供了可能。丝绸之路行记文献的作者们还擅长用多样且细腻的笔触去记叙西部多彩的人文景观,形成了以草原丝绸之路和绿洲丝绸之路为双轴线的文化景观带,极大地丰富了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学景观。另外,研究丝绸之路西行文献还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文体多样性、表现手法的丰富性和西行者们独特而复杂的心路历程。
(一)丝绸之路行记文献对中国文学想象空间的拓展与中国文学地图的重绘
文学想象空间是指文学文本中营造的想象世界,是作者抒写情感、表达理想与寄托心志之所在。早在先秦时期,我国文学格局就开始形成,如《诗经》《楚辞》《论语》《左传》等众多文学作品的出现,既划分了文体的界域,丰富了文学的想象世界,也开始了文学空间的多元建构。随着作家们对中原地区了解程度的加深,他们的求知欲望和观察视野也逐渐投射到当时“中国”以外的地区,而西北这片充满神秘色彩的区域就自然进入了作家的视线,成为文学作品书写的对象,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西北地域文学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穆天子传》和《山海经》。《穆天子传》中的文学空间形态融汇了作者想象、文本描述和读者还原三位一体的立体结构,受当时科学水平的限制,作者构思中的西部尽管以其对客观世界的理解为基础,但面对很多未知的情况,只能建构出一个相对真实而又虚幻的世界。所谓“真实”是指作者是以当时的理解水平去描写,尽管有些描写现在看来极为荒诞,但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却是真实的存在,例如《穆天子传》卷一中对昆仑的描写就有:“□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皇帝之宫。而封□隆之葬,以诏后世。癸亥,天子具蠲齐牲全,以禋□昆仑之丘。”所谓“虚幻”则指作者是在现实基础上进行自觉的文学创作,如《山海经》中就有对西王母形象的塑造:“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穆天子传》和《山海经》中这种“真实”和“虚幻”相结合的描写手法,拓展出更为宽博广大的文学空间。《穆天子传》之后,一直到汉魏六朝时期,西行记作为一种专门记录西北旅行的文体类别开始大规模发展。西行记也成为除诗歌、小说、散文之外,又一独特的文学表达形式。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先民已不满足于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开始了广泛的疆域探索,而在探索过程中,他们往往会借助文学形式将这种生活体验或空间体验符号化,西行记恰好是这种空间体验符号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可见,西行记绝不是对作家行程的简单记录,从其文体内部来看,它是作者以现实空间为基础,结合历史空间而进行的文学想象和空间建构。就此而言,西行记的确拓展了中国文学的想象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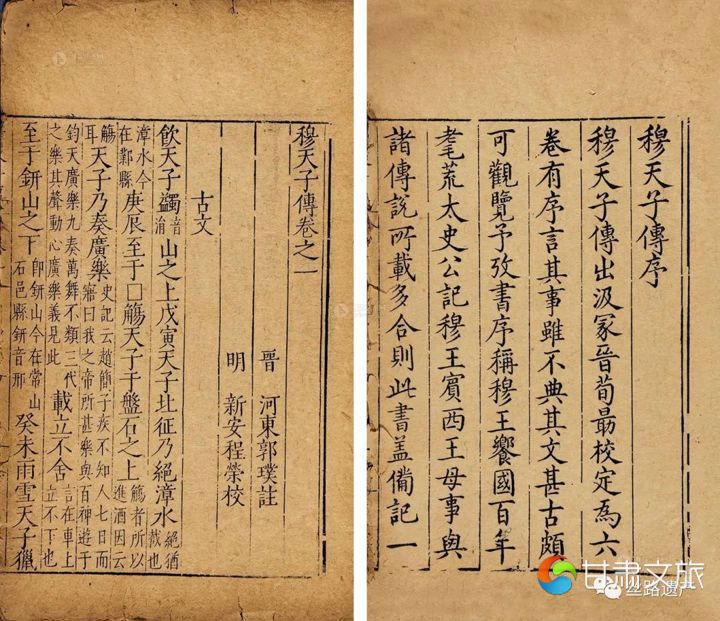
另外,丝绸之路行记文献还有助于中国文学地图的重绘。丝绸之路行记文献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发展、演变的具体规律正好在文学层面体现了中华文化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本质属性和总体特征。首先,中国历史上有不少著名作家如高适、岑参、玄奘、范仲淹、耶律楚材、李志常、解缙、祁韵士、洪亮吉、纪昀、林则徐等因公务、军事、奉诏或被贬等原因在西北工作和生活过一段时间,并留下大量文学作品。通过考察这些作家的西行创作,我们明显感受到他们的西部生活体验对其文学生命形态的形成和转变所起的巨大作用。如作为唐代著名边塞诗人群体代表的高适和岑参,其边塞诗的主要描写对象为西北,要了解高适、岑参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准确把握唐代边塞诗的整体特征,就必须考察他们在西北的具体生活经历及西北特殊地理环境对他们诗歌创作的影响。又如清代著名作家洪亮吉的文学创作和思想在其晚年发生了重大转变,要了解这一转变的原因和过程,就必须解读反映其贬谪伊犁生活的《伊犁日记》《天山客话》等西行著作。所以,从生存空间、心理空间等空间维度对丝绸之路西行文献进行解构,能够打破中国传统文学研究在文学观念、研究方法和基本论题上形成的固化思维模式,为中国文学研究注入新鲜血液和生机。其次,丝绸之路西行文献是中国文学创作的源动力。《山海经》《穆天子传》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描写西部地理与人文的文学作品,关于二书的性质历来多有争议,或云史书,或云地书,或云散文,或云小说,而产生这种争议的原因在于《山海经》《穆天子传》的内容和叙事方式的复杂性,而正是这种复杂性对中国文学影响深远,之后的史学、舆志、小说、散文、游记等基本上都延续和借鉴了《山海经》《穆天子传》的范式。又如,西部地区因少数民族众多,形成了多元而又独具个性的文化。这种文化带有极强的野性和感染力,并通过丝绸之路这条文化交流纽带,跟中原文化进行碰撞和融合。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既对中原文化形成挑战,同时也给中原文化带来了强大的活力。在长期的交流与融合中,西部多民族文学与中原汉族文学形成优势互补、活力互注的生产机制,共同促进了中国文学发展和繁荣。《西游记》就是极好的例证。《西游记》的素材主要来源于唐代《大唐西域记》《悟空入竺记》两部西行记。《大唐西域记》《悟空入竺记》在中原地区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版本的西游故事,明人吴承恩在众多民间故事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使得西游故事定型并焕发出新的生机,《西游记》也跻身于中国小说四大名著之中。可见,丝绸之路西行文献能够深化和丰富中国文学史,并且能为中华文化共同体建设提供新的材料。
(二)丝绸之路行记文献对文学研究新视野的开拓
丝绸之路行记文献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对文学研究视野的拓展和学理体系的建构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丝绸之路行记文献是以古代多民族、多地域、多形态互动的历史实际为前提,以认同中原文学与西部文学、儒家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融合的历史事实为基础,立足于“丝绸之路”和“西部”等独特视角,将作家的西行体验作为书写的突破口,在文体形式、书写方式、作家心态、异域想象等方面都对传统文学创作有所拓展和补充。丝绸之路行记文献的发掘、整理和研究是将玄奘、杜环、耶律楚材、李志常、祁韵士、洪亮吉等人的西行创作置于文化、文学等多重视野中进行系统而深入的考察与梳理,揭示其文本的基本形态,挖掘其独具的审美特质,进而深入丝绸之路西行文献的内在肌理,观察其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从而开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丝绸之路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空间和历史场域,承载了深厚的中原文化积淀、多彩的关陇文化和西域文化特质、神奇的蒙古高原文化元素,可谓兼容并蓄,多元丰富。西行者们作为丝绸之路上的“行者”和文化体验中的“他者”,通过西行书写将“西部”与“中原”两种不同的文化空间在文本中做到了完美契合,为构建中国文学的多维立体格局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把历代丝绸之路西行文献纳入“丝绸之路”和“西部”视角进行审美观照,充分发掘西行文献内在理路,深刻揭示西行文献的深层内涵,不仅有利于拓展古代文学的研究思路,而且为丰富古代文学史书写的空间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和理论支撑。丝绸之路行记文献对西部的想象与建构,为中原地区乃至世界了解“异域”提供了新视角,也为重写中国古代文学史提供了西部空间维度。西部文学和丝绸之路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背景下,丝绸之路行记文献也对古代中国形象的重塑有着重要意义。
(三)丝绸之路行记文献丰富了中国文学景观
文学景观是具有文学属性的自然或人文景观,虽然它以建筑或自然风光为载体,但是又体现出丰富的文学内涵和审美价值。陆上丝绸之路可分为草原丝绸之路和绿洲丝绸之路,沿线的历史文化遗迹和自然景观有邙山、龙门石窟、昭君墓、潼关、华山、骊山、灞桥、太白山、六盘山、关山、阴山、白塔山、五泉山、嘉峪关、玉门关、阳关、火焰山、赛里木湖、果子沟等,上述诸景观均不断出现在丝绸之路西行文献中,是丝绸之路西行文献著录和描写的重点。西行者们正是通过语言文字赋予丝绸之路沿途自然或人文景观以文化内涵,使得其审美价值得以升华,令其具备文学景观的特质。
不难看出,丝绸之路上的文学景观并非单一的个体,它们沿丝绸之路向东、向西延伸,形成了一条辐射东西的丝绸之路文学景观带。古往今来,无数文人骚客来往于丝绸之路,并被西北多样的自然生态和独特的人文环境所折服,这是缘于西北独特魅力所致。但是西行文献的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多为文学家和读者所赋予,故在不同的时空下、不同生活经历的品评者都会赋予同一景观以不同的意义,使得丝绸之路西行文献所塑造的文学景观具有丰富的内涵。以文学景观内涵的多样性为媒介,我们还可以了解到西行者思想情感的复杂性,如“关山”,在地理学家看来仅仅是一个山脉的名称,但在军人来看却是保护长安的屏障,在商人们看来又是追逐财富的最后一道障碍,在西行的文人们来看却是一个抒情言志的意象和追溯历史的符号。正是由于文学景观层叠累积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想象,赋予了关山等自然景观丰富的价值。丝绸之路文学景观除显现的文学价值外,还蕴含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建筑学、美学等方面的独特价值。因此,在“一带一路”伟大战略倡议下,运用文学、历史学、文献学的研究角度与研究方法深入开掘丝绸之路行记文献的文学价值将有着多重重要意义。
(四)丝绸之路行记文献对作家行迹和想象空间的拓展
丝绸之路行记文献中,详细载录着西行者们的活动轨迹,蕴含着西行者们丰富的想象。随着玉石之路的开通,我国先民的足迹开始向未知的西部地区扩展,打破了人们相对闭塞的生活状态,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也不再偏于一隅,《山海经》《穆天子传》中对“中国”以外地区的描写正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写照。汉武帝时期,张骞“凿空”西域,中西交通恢复,许多作家活跃于丝绸之路,并且出现了大量记录西行见闻的作品,遗憾的是这些著作多已亡佚,仅有零星记载散落于史志文献中。据《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书中所载西行文献可知,这一时期作家活动的范围多集中于西域,最远至安息(今伊朗)和印度等地。六朝至唐宋,由于佛法东传,西行求法运动在国内兴起,印度开始成为行记文献的主要描写对象,行记文献的内容也多反映西域及印度的交通、地理、民俗、宗教等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唐朝时由于国力空前强盛,丝绸之路贸易也格外繁荣,虽然印度仍然是西行著作描写的重点,但是在唐代西行文献中作家的行迹开始向中亚、西亚及地中海一带拓展。这也表明,唐朝时中国作家的文学想象空间扩展到了中亚、西亚和地中海等广大地区。元初,随着成吉思汗西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间广阔的疆域,也为文人们提供了较前代更为开阔的书写空间。明朝时,受国家政策的影响,文人多在嘉峪关以东地区活动,直到清朝这一局面才得以改变。清朝时,中央政府重视对西北地区的开发,将大量内地百姓和获罪的官员、文人迁移到新疆,使得文人们再次踏上了西部这片存在于历代文人想象中的土地。
可见,由于受政治、经济、交通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历史时期的行记文献呈现出作家不同的活动轨迹,蕴含着作家精彩的想象世界。仔细梳理、全景式呈现西行作家的人生行迹、文学活动和行记作品,不仅能够改变我们对文学地理空间的认知方式,细化并拓展文学史的时间和空间维度,还能集成文史资源,构建文学和文化知识图谱,还原文学历史现场。
(五)丝绸之路行记文献丰富了古代文体与文学表现手法
我国古代的诗、文、序跋等众多文类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特性和表现手法,在具体创作过程中也要遵循其文体的基本规范。丝绸之路行记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也有其文体规范。与其他文体一样,行记在保持文体独立的同时,也在不断吸收其他文体的优点,在体裁、写法、风格等方面不断完善。西行记在先秦时期采用“地名+风土”的类地志的描写方式,体现出的文体特征不明显。至六朝时期,随着文学理论的发展,文体间的相互影响越来越深入,西行记吸收了史书中人物传记的写法,出现了以人物为中心的行传体行记。除行传体行记外,六朝时还出现了一种以记录行程为中心,记事比较松散的行记体行记。从六朝到唐代,行传体行记和行记体行记一直是西行记创作的主流。到了宋代,受唐代古文运动影响,文人立志于文学理念的革新,这一文学革新理念也波及到西行记创作中,使得当时的西行记创作虽然以行传体行记为主,但也出现了一些行程录体和日记体行记作品。到了清代,西行记创作进入高峰期,行记文体中开始大量出现日记体,此外也有少数行程录体和笔记体行记问世。可见,从先秦至清代,西行记在文体方面不断吸收和融合新的文体样式,从行传体、行记体发展为日记体、行程录体和笔记体等文体种类,既体现出行记文体多样性,也大大丰富了古代文体。
丝绸之路行记文献除丰富了我国古代文体外,还在文章结构、叙事、语言、文风和情节等文学表现手法方面进行了探索。如西行记一经诞生,就形成了以“纪行+见闻”为线索的叙事模式,在不断的发展和流变中逐渐形成了分别以日程和人物生平事迹为叙述主体的典型体例。从具体叙述模式来看,以行程时间为叙述主体的行记,一般采用“行程时间”为主线,在山川、城邑之间不断转换空间,以经济、文化地理为主要记述对象。以人物生平事迹为叙述主体的行记,多以个人的活动轨迹为主线,并以风景名胜、社会生活和人文胜景的描述夹杂其中,极富人文情趣。需要注意的是,出使类行记尽管以“日程”为线索,但由于作者多受传统史学观念影响,在行记内容的选择中有意降低地理和纪行的比重,多侧重于对当时政治环境、出使时所遇到的问题及应对措施等史事的载录。从叙事手法来看,早期的西行记多以平铺直叙的方式记录事件的完整过程,记事简单而粗略。唐以后,西行记中开始广泛采用日记体形式,西北的地理地貌、物产风情和交通情况逐渐成为西行文献记述的重点,这正是行记文体的叙事功能得到加强的表现。随着日记体行记的流行,西行文献的记录单位也逐渐以日程为主,按日记事,明显扩大了文体的容量,将行经路线、沿途见闻、每日行程等一一呈现,使得内容更加详实,并且在叙事上都紧扣西行历程来载录,不枝不蔓,条理清晰。
在语言上,因唐以前的西行记作者多为文化程度不高的僧人,故其作品多用质朴无华的文字去记叙西行见闻。而在唐代以后,随着僧人文化程度的提高和作者身份的转换,西行记创作的语言越来越丰富,文学语言成为创作主体,如《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就一改前代僧人记事粗糙的情形,在叙述见闻时开始有意识地使用四六句式,间以散句,使得行文更加流畅,句式富有美感,抒情性也大大增强。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了清代,如祁韵士、洪亮吉等人创作的行记往往散韵相杂,错落有致,注重抒情和文章的美感,较之于唐以前的行记更体现出行文的音乐美和不对称之美。在文风上,因行记文献作者众多,不同作家个性不同,其作品也呈现出不同的文风。在西行文献创作的萌芽期,受文体功能、叙事手法和语言方式的影响,行记作品多侧重于对行程及地理的记录,有着明显的史志文献的特征,故这一阶段西行文献的风格并不明显。唐以后,一直到清代,因西行文献创作中叙事手法和语言方式逐渐丰富,再加作家气质禀赋的不同,行记的文风也呈多样化特征。首先,行记内容充实,记述有趣。如清代西北行记短则一卷,长则十余卷,或议论,或记叙,或写景,或抒情,都能令人读后有所启发。如裴景福《河海昆仑录》即长达6卷,20多万字。裴景福在流戍途中仍十分关心时局,而当时清政府内部对于“海防”“边防”孰重孰轻存在激烈的争议,裴景福在其亲临西北后,深刻地意识到西北边防对于清朝国防尤为重要,他认为“塞外空阔,虽有戈壁瀚海之阻,而土人沙线分明,处处可通,坚壁清野之法,势不能行,若不西扼塔喀,东联甘陇,究无立脚之地。……即如新疆,我得之不过西北藩篱耳,万一为人所有,则长驱直入,高屋建瓴,足以拊中原之背,而扼其吭,南失越南,东失朝鲜,尚可苟延支撑,若天山西倒,瀚海东奔,欲苟延支撑而不可得矣”。作者在谈到西北社会问题及边防的重要性时,常常借助典型事例进行论述,写一件事往往洋洋洒洒用几百言,且叙述清晰,全无拖泥带水的弊病。其次,行文变化较多,词汇、句型和文章结构、风格等呈多样化态势。西行记创作发展至清代,词汇越来越丰富,句型灵活多变,文章结构灵巧讲究。行记的风格也多种多样,或华丽,或质朴,或典雅,或平正,个别作品甚至将华丽与质朴兼融为一体。再次,叙写精妙细致。清代以前的西行记,因注重地理记录而忽视文章写作,行文多流于粗糙,但是到了清代,西行者们在下笔记录自然风景和名胜古迹时往往会仔细推敲,字斟句酌,使得描写更加集中、贴切,绝无粗制滥造之嫌。清代西北行记的代表作品,如钱良择的《出塞纪略》、张寅的《西征记》、景廉的《冰岭纪程》等,都具有这种特质。
从情节来看,唐前西行文献中除《法显传》《宋云行记》外,很少有细节描写,而《法显传》《宋云行记》中的细节描写也不多。如《法显传》中载:“住此冬三月,法显等三人南度小雪山。雪山冬夏积雪。山北阴中遇寒风暴起,人皆噤战。慧景一人不堪复进,口出白沫,语法显云:‘我亦不复活,便可时去。勿得俱死。’于是遂终。法显抚之悲号:‘本图不果,命也奈何!’复自力前,得过岭。”此处,作者在写到小雪山时,增加了对同伴慧景之死的全过程描写。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行记已经注重细节描写,但仍然比较少见。唐代行记中,细节描写已经被广泛运用于景物、场面、对话的写作中,行记作品也更具情采。到了清代,西行记中的细节描写尤为突出,如黄濬的《红山碎叶》写道:“满汉两城元宵灯火最盛,汉城尤盛于满城。……惟秧歌最丑怪,一人扮白髯花面红缨帽,白皮短褂反穿,手执伞灯领队。数人扮如魑魅魍魉,花衣蓬首;数人扮如武士;数人扮如浪子;数人扮如娼妓,粉面如涂墙,强作娇态。白髯者跳跃彳亍以歌,则余人跃舞旋转以和之。旁击大锣大鼓,聒耳喧阗。数折俱毕,一浪子掷巾于地,一娼妓装者歌觅备丑态,歌觅数回,忽然拾巾以去,哄然群散,又往一家。”可见黄濬在叙述乌鲁木齐元宵节的社火表演时,已经不再是对秧歌表演的整个环节进行机械复述,而是在记述中增加了对表演者服饰、面部表情和表演场景等细节的描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如景廉的《冰岭纪程》云:“人马履冰而行,高下曲折,极崎岖之致。偪仄处仅一线,异常危险,揽辔徐步,心旌摇摇。冰坼处,塞以驼马之骨,挥鞭竟过。下有水声澎湃震耳,目不敢视,亦无暇视。……少坐,徒步下岭。冰梯数百仞,明如镜面,曲折而下,极陡极滑。四围冰凌矗立,如置身水晶域中。梯上铺毯,左右扶掖,否则寸步难移矣。下岭后,乘马行。冰岗起伏,仍须登降,猱升鹘落,备诸艰险较岭北尤甚。时已薄暮,暝烟四合,川谷纠纷,对此茫茫,百端交集。”景廉在描写新疆冰岭道路的艰险难行时,即通过天气、环境,以及过岭人的内心世界剖析等细节描写来烘托冰岭道路之险峻。
(六)丝绸之路行记文献记录了西行者的心态
丝绸之路行记的作家们在进行创作时并不是对西行见闻进行简单的记录,他们往往将自己的体验与感受投射到作品中。如果仔细研读文本,透过那些充满真挚感情的文字,我们将会体悟到隐藏于文字背后的作者们纤细的内心活动。行记文献有诗歌,也有散文,其中行记因其字数不受限制,不乏有如《河海昆仑录》《辛卯侍行记》等字数达数十万之巨的长篇纪行散文,故一部西行记的时空跨度之广是游记所无法比拟的,所表现的情感也并不单一,饱含了作者在旅行途中所有的喜怒哀乐。如《大唐西域记》载:“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详国俗之刚柔,系水土之风气,……记诸慕化。斯固日入以来,咸沐惠泽;风行所及,皆仰至德。”大清池“周千余里,东西长,南北狭。四面负山,众流交凑,色带青黑,味兼咸苦,洪涛浩汗,惊波汩淴,龙鱼杂处,灵怪间起”;“瞢揭厘城东北二百五六十里,入大山,至阿波逻罗龙泉,即苏婆伐窣堵河之源也。派流西南,春夏含冻,晨夕飞雪,雪霏五彩,光流四照”。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亦有“行十余里,自念我先发愿,若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今何故来?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于是旋辔,专念观音,西北而进”的记载。可见二书在记述玄奘西行求法这一具体事实时,会在行文中掺杂对唐朝盛世的自豪与歌颂、对壮美山河的赞美、对“西域”异域风情的折服,还表达了对西行求法的坚定信念等众多情绪。又如祁韵士在《万里行程记》开篇便写道:“时经一百七十余日,路经一万七百余里,所见山川城堡、名胜古迹、人物风俗及塞外烟墩、沙碛,一切可异可怖之状,无不周览遍历、系于心目。”作者虽远赴贬谪之地,但字里行间不见任何怨天尤人的悲愤语词,将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态度在行记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再如洪亮吉,他因事贬谪伊犁,在赴伊犁的路程中,因朝廷有“不许作诗,不许饮酒”的禁令,所以他只有寓情于景,通过记录自己行程的方式来表达内心丰富的情感。所以,洪亮吉的西行著述中表现的是他对自身命运的担忧、对清朝统一天山南北盛举的赞美、对故土的思念等复杂情感。又如林则徐,他所生活的晚清时期,国家山河破裂,西方“现代”观念猛烈冲击国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的《荷戈纪程》《乙巳日记》等较祁韵士、洪亮吉等人的行记而言,其写作中已较少对国家及西北山河的赞美,更多的是通过对西北地理、军事的考察分析后所表现出来的对西北边疆安全的忧患意识。可见,这些丝绸之路西行文献内容丰富,能够真实地反映出两千多年来游走在丝绸之路上的文人们的心理活动情况,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总之,丝绸之路行记文献对于我们研究西部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发展与演进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一座尚未被开发的富矿,随着研究的深入,其蕴含价值将会得到越来越清晰的呈现。 来源 :“中国历史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本文采摘于网络,不代表本站立场,如果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