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回忆本人征聘来敦煌文物研究所(后为敦煌研究院)从事敦煌遗书研究工作经历,从通读敦煌遗书开始接触并熟悉研究对象,写记大量笔记,积蓄资料,充实空乏,从不知到有知,从外行变内行;研究路径,则由点到面,由低到高,从特殊带到普遍,以见端由。
【关键词】 敦煌学;敦煌遗书;研究路径
一 敦煌文物研究所一纸征聘改变我人生之路
1958年4月,大学毕业前夕我被划为“右派”,“开除学籍,劳动教养”,从此打入“另册”。解除“劳教”后回故乡河南正阳县务农。不幸遭逢旱灾,家口难以活命,遂“自流”新疆,到米泉县羊毛工村当了16年的农业社“另册”社员。1979年3月,武汉大学为我改正“错划右派”问题,恢复学籍,补发大学本科毕业文凭。此前,我已经在新疆米泉县第一中学担任两个高中毕业班语文课的“民办教师”,改正“右派”后,由于家属子女户口皆在米泉县,我只得回新疆米泉一中仍操旧业,只是“民办教师”变成了“吃皇粮”的“公办教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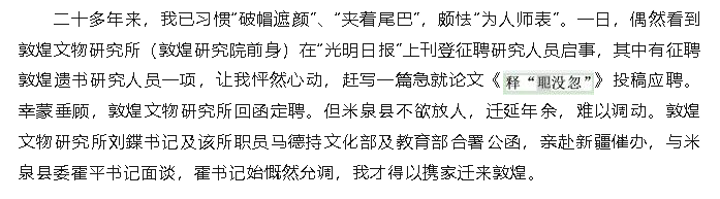
1982年5月2日到达莫高窟,时年48岁,殆近“迟暮”,却贸然踏上异途陌路。有人写我“从泥腿子到敦煌学家”(《中华儿女》杂志,1997年第7期:《从泥腿子到敦煌学家的李正宇》)。“泥腿子”,可谓“名副其实”,但“敦煌学家”的大帽子我却愧不敢当,因为我被“大帽子”压顶20年,刚刚扔掉“大帽子”,一心挤进敦煌学队列“荷戈”驰驱,哪敢矜执“高冠”招人嗤鼻!
二 敦煌遗书把我带进敦煌学大门
到达莫高窟时,莫高窟南区新建的住宅楼刚刚完工,正待验收,我家暂住莫高窟招待所。段文杰所长(后为敦煌研究院院长)来家看望,让我到敦煌遗书研究室从事敦煌遗书研究,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表示正合夙愿,同时坦诚表明,我对敦煌遗书是“门外汉”,需要半年时间熟悉敦煌遗书,然后才有条件上岗从事研究工作。段先生慨然答应半年之内不给我分配其他任务,一年之内不要求我拿出研究成果。并且告诉我,敦煌遗书研究室有英、法及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缩微胶卷和缩微阅读器,资料室有可观的图书资料,可供使用。
段文杰所长的一席话,让我定下心来,开始阅读敦煌遗书,钻入敦煌遗书大海,进行填鸭式的“恶补”。先是普读黄永武教授编《敦煌宝藏》140册,继在阅读器前通读英、法、北图所藏敦煌遗书缩微胶卷及日、俄零星藏卷(当年,日、俄藏品很少刊布),做了400多张卡片,摘记30多万字笔记,成为当年普读敦煌遗书少有学者之一。我用数月时间跑步进入敦煌学大门,为从事敦煌遗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可见“阅读敦煌遗书”成为我跻身敦煌学大门的“敲门砖”,不比今时青壮年敦煌学者通过修学敦煌学硕士、博士那样可以安步进入敦煌学大门,走上研究岗位立可操戈上阵,条件优我远甚。
1982年末,我到敦煌文物研究所不满一年,受任敦煌遗书研究室副主任。1983年5月,获文博专业助理研究员职称。1984年8月,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敦煌遗书研究室随之升格为敦煌遗书研究所,施娉婷先生任所长,我为副所长。1988年元月,我获文博专业副研究馆员职称。1989年施先生退休,我接任所长。1990年,敦煌遗书研究所迁来兰州,我申请将敦煌遗书研究所改名敦煌文献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呈请甘肃省政府批准,遂改新名、颁行“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公章。1993年3月我获文博专业研究馆员职称。2000年元月退休,继而返聘为研究员至今。期间,又被兼聘为西北师范大学及兰州大学兼职教授,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从“泥腿子”变身为“敦煌学者”,正是敦煌文物研究所暨敦煌研究院为我铺设了一条光鲜之路!
三 研究路径由点到面,由低到高;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

我上小学、中学期间,读了不少新旧小说、新旧诗集,对文学产生极大兴趣,想当作家,所以报考了武汉大学中文系。大学三、四年级修习必修课之外,还选修了刘赜教授《汉语音韵学》、刘永济教授《楚辞研究》、席启駉教授《史记研究》、程千帆教授《杜甫研究》及沈祖棻教授《宋词研究》,对古代文学产生偏好,也打下了古汉语知识基础,兴趣转向古代文学。不幸在毕业前夕成了“右派分子”,沦落为时代“弃儿”;“壮志蒿莱”,义气沉埋。所幸尚存古汉语基本知识未被剥夺,为此后跻身敦煌学架起桥梁,成了敦煌学“分子”,一个学文学的,却干起了对我来说则是“破门”之学的“敦煌学”。
我从事敦煌学研究,就是借助古汉语知识阅读敦煌遗书起步的。在熟悉敦煌遗书的基础上,从点滴小处着手,打造并筑牢基点,然后横向扩展到面,进而打开眼界向纵深发展。具体说来,是从阅读敦煌遗书入手,一砖一瓦地累砌从事敦煌遗书研究工作的基础;然后才敢开始试作敦煌遗书研究。我来敦煌文物研究所后撰写的第一篇敦煌学论文是《吐蕃子年(公元808)沙州百姓氾履倩等户籍手实残卷研究》。此文是我进入敦煌学之门的敲门砖,我由此进入了敦煌学研究的大门。
《吐蕃子年沙州百姓氾履倩等户籍手实残卷》本是敦煌遗书的一件写卷,编号S.3287。我对这样一个断残写卷进行研究,也是从基础工作作起。由点到面,逐步扩展。首先对原卷进行注释。“注释”是对不明的词语、不懂的事物加以解释,通过解释,才可以读懂原卷。所以“注释”也是一种研究,是基础性的研究。读懂了原卷,才可能对原卷进行扩展的研究。
我在对《氾卷》做出注释、读懂弄明之后,进而对《氾卷》的内容、事项、含蕴诸问题展开探讨。探讨的做法则是进行横向铺展、纵向深入,就是从《氾卷》中提出下面八个问题加以讨论。这八个问题是:
1、考证其制作年代。这关系到吐蕃统治敦煌进行户口调查的时间、性质;
2、通过对《氾卷》登录项目的考察,推测此次户口调查的意图;
3、探讨《氾卷》的文体格式及其文体学意义;
4、根据《氾卷》原有注记,推断“将”级机构为吐蕃统治敦煌居民的基层组织机构;
5、《氾卷》反映吐蕃贵族掠夺人口为奴;
6、考察人口年龄登录的规律及人丁年组的划分(这一节所用的“五步分析法”尤堪玩味);
7、对《氾卷》各项统计概率及若干问题进行讨论;
8、根据《氾卷》各项统计概率,推测当时敦煌人口。
将上述一个个点积聚成面,结集成果,完成论文,结束该卷的研究工作。
此文颇获好评。汪泛舟先生告诉我,他的一位学界好友读了此文说:“《吐蕃子年(公元808)沙州百姓氾履倩等户籍手实残卷研究》是一篇真正的论文,堪称范文。”我给研究生讲课时,曾用此文作研究敦煌卷子的一种方法进行讲授,颇有助于学生学写论文之入门。
从撰写《吐蕃子年(公元808)沙州百姓氾履倩等户籍手实残卷研究》之后,继续积聚资料,积累知识,才敢于进行系列性研究(如《唐宋时期的敦煌学校》,《敦煌方音止遇二摄混同及其校勘学意义》,《关于金山国和敦煌国建国的几个问题》,《沙州古城谈往》,《唐宋时代敦煌县河渠泉泽简志》,《敦煌地区古代祠庙寺观简志》,《再论晚唐五代北宋时期的敦煌佛教》等文)。
举例来说,我在阅读敦煌遗书时,对其中“学郎题记”颇感兴趣,所以随手摘记,后来加以整理,将一条条零落散乱的題记,汇辑为《敦煌学郎题记辑注》,竟成一宗专史资料,对研究敦煌学校教育、学校类型、分科教材、读物抄造、学郎作业、学郎情趣以及敦煌人物及敦煌写卷的系年考证等等都有参考价值。我撰写《唐宋时期的敦煌学校》,主要依据就是《敦煌学郎题记辑注》(《敦煌学郎题记辑注》写作在前,而发表在后)。可以说,零星的“学郎题记”汇辑成《敦煌学郎题记辑注》,为撰写《唐宋时期的敦煌学校》筑造了基础,甚至可以说是《敦煌学郎题记辑注》的脱胎换骨。
又如:我对敦煌一所所祠庙寺观资料进行摘录,制作百余张卡片,积累了不少资料。时逢编辑《敦煌学大辞典》,约我撰写敦煌祠庙寺观词条。后来《敦煌学大辞典》的编辑出版工作一度搁浅,我将所写敦煌祠庙寺观词条加以整理,撰成《敦煌地区古代祠庙寺观简志》发表。我又从敦煌遗书及《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中搜集敦煌佛教僧尼信众种种信行及处世作为资料,条分缕析,陆续写出下列相关诸文:
《莫高窟第九十八窟历史背景与时代精神》
《敦煌俗讲僧保宣及其〈通难致语〉》
《所谓“三教融合”——以佛教为中心的考察》
《孝顺相承,戒行俱高——论中晚唐五代宋敦煌佛教高张孝道》
《吸纳消化 化彼为我——谈莫高窟北朝洞窟“神话、道教题材”的属性》
《佛塔丛识——从建筑、雕塔到剪刻塔、写经塔》
《晚唐至宋敦煌僧人听食“净肉”》
《晚唐至宋敦煌僧尼普听饮酒》
《晚唐至宋敦煌听许僧人娶妻生子》
《8至11世纪敦煌僧人从政从军》
《敦煌僧尼生活面面观》
《唐宋敦煌世俗佛教的经典及其功用》
《敦煌佛教研究的得失》
《唐宋时期的敦煌佛教》
《再论中晚唐五代北宋时期的敦煌佛教》
综上所得,顺理成章地揭示出八至十一世纪敦煌佛教“入世合俗,戒律宽松;既求来世,尤重今生;亦显亦密,亦禅亦净;和合众派,诸宗兼容;不别真伪,众经皆奉”的特点,改塑了向被歪曲的敦煌佛教类型。这样的佛教,不见经传,无所称名,余为拟名曰:“敦煌世俗佛教”。这项系列性研究,又是“由点到面,由低到高;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又一例证。
借此机会我还愿意谈谈偶然撞入另一“破门之学”——“中国书法史”研究。
1990年冬,从电视上看到某书法家讲硬笔书法,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钢笔传入我国,国人用钢笔写汉字,由此产生汉字硬笔书法。但我从敦煌遗书中确知汉、唐、五代已有为数可观的佉卢文、汉文、婆罗谜文、突厥文、梵文、回鹘文、于阗文硬笔书法。而时人多有未知。应当把敦煌古代硬笔书法介绍出去,以正视听、而广见闻。1992年冬,撰成《敦煌古代硬笔书法》一文,指出敦煌古代硬笔书体的笔画特点是“曲直唯线,点不像桃,肩、勾不顿,撇不作刀,捺不出脚,锋芒昭昭。”此文草成,恰值友人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主任金荣华教授为创办《文化大学中文学报》约稿,遂将《敦煌古代硬笔书法》一文寄付荣华教授,于1993年2月在台北《文化大学中文学报(创刊号)》头条刊出。
书法家、考古学家及美术史家一般都认为,3000多年来的中国书法就是毛笔书法,硬笔书法仅是19世纪钢笔传入之后的事。但我揭示出敦煌文献中保存的两万多页硬笔写本,以“实物”推翻了中国古代没有硬笔书法的旧说,打破了毛笔书法“一统天下”的中国书法旧史观,改写了中国书法史。
1993年春,我将此文扩写为《中国唐宋硬笔书法——敦煌古代硬笔书法写卷》。同年5月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当年仅印行3000册,出版社大部分拿到香港展销,很快售罄,少部分在国内出售,也很快售罄。我有20本样书,送朋友或友人索取,最后仅存的一本,也被杜斗成教授代其武汉朋友索去。后来河北唐山县书法家李金河先生函索此书,我告以愧无可赠。后,金河先生设法从上海文化出版社藏书购得,反而寄我一本。如今我所保存的,就是金河先生送我的那本。
为了进一步追索中国硬笔书法产生、发展的历史,我从近300多种古籍、今著中辑录300多条有关硬笔书写的资料,编为《中国古代硬笔事略》(近来续增至500多条)。在此基础上写出《硬笔书法是中国书法的母体》,在郑州《寻根》杂志1994年第2期发表。1995年11月,在我并未申请且毫不知情的情况下,95全国硬笔书法理论研讨会组委会授予拙文“硬笔书法理论研究特等奖”。继而,我发现甲骨文、钟鼎文,大篆、古隶等先秦文字兼有硬笔书写的本然书体和多笔描画而成的加工字体——两种不同的字体。
从上古之硬笔书体及加工描画字体的揭示得到启示,获知我国上古时期之“本体文字”皆属硬笔书体,进而又从战国简牍得知,战国简牍见有毛笔书字。而战国简牍中的毛笔字,并没有创立具有毛笔特点的毛笔书体,例如西汉隶书、八分、章草、行草之类,却寄身于硬笔书法的“本然书体”。可证战国时期虽有毛笔书迹,却无毛笔书体。由此得知我国书法史从殷商到春秋时期,唯硬笔书法独霸书坛,战国时期毛笔书写初露头角,后至西汉,毛笔书体大行于世,而硬笔书法很快退居下陈,但仍存活下来,悄然行世(如竹箸书字,刀锥刻字,划地书字,铅笔书字,荆笔书字,竹箨书字,屈指画地,白土书字,手杖划字等等)。从西汉以来,我国书法史便沿着毛笔书法和硬笔书法两条线索、两大系列继续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硬笔书法重新抬头,在实用书写领域渐渐取得优势。
如此,我对中国书法史有了新的理解,形成与众不同的书法史观。于是改写《中国唐宋硬笔书法——敦煌古代硬笔书法写卷》为《敦煌古代硬笔书法》,并撰写《中国书法史观的革新与重建》为附编,书名改为《敦煌遗书硬笔书法——兼论中国书法史观的革新》,于2005年12月在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2007年8月,加以增补修订,在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简体字版。期间,陆续发表《建构中国书法史的新体系》、《谈我国书法史的三个时期》、《论汉字书法史分期问题》、《中国书法史必须改写》等文。研究之路由低到高,逐步推进。之后又由博返约将我关于中国硬笔书法的探索,括略凝缩,撰为《硬笔书法是中国书法的源头、母体和通脉》,应邀在2011年9月深圳《硬笔书法高峰论坛》上作主题报告,获终身学术成就奖。并由此被中国硬笔书法协会聘为学术顾问。
2023年12月,値中国硬笔书法协会成立30周年之际,中国硬笔书法协会认为笔者在“中国文字的书写发展变革历史学术研究方面成就卓越,尤其是对古代中国硬笔书法的研究做出突破性重要贡献”(中国硬笔书法协会颁授《荣誉证书》及奖牌题词),授予笔者“学术研究终身成就奖”。

高评如许,出乎望外。我在敦煌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似不足与中国书法史研究相比肩,不免歉然有憾焉!
作者简介:
李正宇(1934- ),男,河南省正阳县人,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从事敦煌历史、地理、文化、佛教、语言研究。 来源 :敦煌研究院
本文采摘于网络,不代表本站立场,如果侵权请联系删除!





